欙鳇茽餐新闻网
几年(nian)前的某一(yi)天,挪威作家西蒙·斯特朗格得知,自己岳母从小居住的房子(zi)曾是纳粹挪威间谍亨利·林(lin)南盘踞的处所,而她的祖父希尔施·科米(mi)萨尔就(jiu)死(si)于挪威的犹太人大屠戮。
这栋被称为“罪过的修道院”的房子(zi),成为斯特朗格探究和书写家族史的开始。他以“辞典体”的形式,将科米(mi)萨尔的家族史、亨利·林(lin)南的故事与(yu)二战时期的残酷历史交织,写成了(le)《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
在这部历史小说里,他想要揭破某种(zhong)“只有虚构作品能力传递的真(zhen)实(shi)”,迫令人们去(qu)思索暴力的来源和阻止暴力的可能方式。
日前,斯特朗格携《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中译(yi)本访华,他在上海接受了(le)澎湃新闻的专访,“说话能够让(rang)人产生(sheng)隔(ge)阂,但人与(yu)人之(zhi)间应该有更(geng)多相通的东(dong)西”,他说道。

西蒙·斯特朗格(Simon Srranger, 1976-)
说话能够是暴力的开端
展开盈余 91 %澎湃新闻:书名《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据说是从挪威语直译(yi)而来,而英语版的译(yi)名是“继承念出(chu)他们的名字(zi)”(Keep Saying Their names),在这本书里,这两个表达的干系是怎样的?对你来说,辞典和记(ji)忆有甚么干系?
西蒙·斯特朗格:挪威语的书名是没有可译(yi)的,在英语里找没有到符合的直译(yi)。当时,我的出(chu)版代理商发起引用这本书最(zui)后的几句话,从中获得了(le)书名。我以为这个标题(ti)很美,但在挪威语原版中,书名大致(zhi)意思是“灼烁与(yu)阴郁的百科全书”,我更(geng)喜欢这个标题(ti),由于我想写的是一(yi)部百科全书式的小说,它(ta)关乎说话。
我想,一(yi)部词典大概一(yi)部百科全书报告的是世界上的一(yi)切。它(ta)应该是搜罗万(wan)象的,而我在小说里所做的是选择这个世界的一(yi)部分去(qu)报告,我们的记(ji)忆也是如许运作的。记(ji)忆是私家的,这部小说也是一(yi)部异常私家化(hua)的“百科全书”。

《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书封
澎湃新闻:你在之(zhi)前的讲座上谈到,这部小说底本要写的是发生(sheng)在“罪过的修道院”相反房间在没有同时间的故事,如许的计划最(zui)后是怎样发展成辞典的结(jie)构的?
西蒙·斯特朗格:早先,我只是记(ji)录下(xia)了(le)没有同时间发生(sheng)在各个房间里的一(yi)些片段,但后来,我将这些片段移动(dong)和分开,为故事制作新的入口和出(chu)口。在我决意以辞典的形式来完成这部小说之(zhi)前,差没有多只有30页,我希望让(rang)整个小说像百科全书那样展开,因而它(ta)逐渐雄厚起来。
我希望辞典的编排能给读者带来欣喜:你永远没有知道下(xia)一(yi)页会发生(sheng)些甚么。借由辞典的结(jie)构,亨利与(yu)我老婆(zi)家族的故事线(xian)彼此交织。我能够在我想要的时候停下(xia),也能够写一(yi)些很短的文字(zi)——对我来说,说话的诗性和音乐性对我来说很重(zhong)要,我一(yi)直试图把它(ta)们写进小说里。
以辞典的方式来写这本书还有一(yi)个原因:它(ta)让(rang)人关注到说话本身。大屠戮老是从说话开始的,说话没有是无(wu)辜的,说话是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是它(ta)让(rang)我们以为彼此之(zhi)间有不合。那正是暴力的开始,是对或人采用(qu)反(fan)对行动(dong)的开始。小说的辞典结(jie)构展现了(le)说话本身和它(ta)的影响。
澎湃新闻:小说中那位臭(chou)名昭(zhao)著的亨利·林(lin)南早先是个普通的挪威人,从小受到四周(wei)人的欺凌,在想要摆脱这一(yi)处境的历程里,最(zui)终(zhong)成了(le)挪威犹太人大屠戮里最(zui)残酷的凶犯。这让(rang)人遐想到汉(han)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所写的“平庸的恶”,你以为林(lin)南和艾希曼是统一(yi)类人吗(ma)?
西蒙·斯特朗格:我以为林(lin)南没有是生(sheng)来就(jiu)是怪物(wu),这一(yi)点很关键,这也是我从他的童年(nian)写起的原因。当一(yi)个人成了(le)像林(lin)南那样的怪物(wu),形成了(le)那末多的死(si)亡和痛苦,这个历程中发生(sheng)了(le)甚么?我想要去(qu)理解这种(zhong)变更(hua)。小说里林(lin)南的每(yi)幕都是基于真(zhen)实(shi)的历史事件,包含他的第一(yi)次出(chu)场:他和他的弟弟一(yi)起出(chu)现,弟弟衣着女士鞋子(zi),由于他的冬靴破了(le),这让(rang)他遭到了(le)嘲(chao)笑。林(lin)南从小被霸凌,我以为这是一(yi)切的开端。
我以为林(lin)南和艾希曼没有同。阿伦特提(ti)出(chu)的“平庸的恶”对于研究整个大屠戮历史当然都很重(zhong)要。比如在挪威,警员逮捕犹太家庭(ting),没有是出(chu)于对犹太人的恨,而只是他们被示知要这么做:总得有人进行逮捕,有人开车,有人将犹太人送上船,有人在船上事情,有人建造运输的火车,最(zui)后,有人制作毒气室。每个人都只是做了(le)自己那一(yi)小部分的事情,结(jie)合在庞大的呆板中,最(zui)终(zhong)杀死(si)了(le)约莫六百万(wan)人。但林(lin)南和这些人没有同,他异常积极地饰演着自己的脚色:当他被要求成为纳粹的隐秘特工,“渗出”挪威抵抗组织的任务时,他是真(zhen)的投入其中,没有只是依照吩咐的去(qu)做,而是依照他自己的想法去(qu)做。除了(le)为他自己做事之(zhi)外,他没有任何意识(shi)形状:我想,若是挪威抵抗组织吸纳他,想要让(rang)他做事,他可能也会去(qu)做。
有很多像他如许的人,而他是战争、第三帝国与(yu)自我人格最(zui)没有幸的结(jie)合,纳粹和战争给他带来了(le)款项和武器,让(rang)他去(qu)杀戮和折磨别人。他的人格是破碎的,被别人疏远隔(ge)离了(le)太久(jiu),然后他说:“我比任何人都要好,我没有想成为他们中的一(yi)员。我会向(xiang)他们展现我有多么伟大。”而这恰好是自大的标志——当你冒充更(geng)壮大更(geng)厉害的时候,你更(geng)懦弱。
澎湃新闻:对于本日的读者来说,你希望通过林(lin)南的故事向(xiang)他们报告甚么?
西蒙·斯特朗格:我以为跟着我越写越多,我开始思索本日的年(nian)轻人,他们中有一(yi)些脱离了(le)现实(shi),在网络上获取(qu)信息。2011年(nian),一(yi)个年(nian)轻的挪威可骇份子(zi)杀了(le)77个挪威人,其中大多是青少年(nian)和儿童。这个人的信仰完全就(jiu)是纳粹意识(shi)形状的延(yan)续。我想他可能和林(lin)南有异样的想法,只是他的动(dong)机更(geng)多出(chu)于意识(shi)形状。
这就(jiu)是我想对本日的读者说的:在这些年(nian)轻人变得极度之(zhi)前,去(qu)认识(shi)他们,实验回收他们,试着让(rang)他们感(gan)到恬静,感(gan)到自己是被赏(shang)识(shi)的。我以为被伶仃和被抛下(xia)对于人类来说是最(zui)痛苦的事情之(zhi)一(yi),可能会酿成很严峻(zhong)的结(jie)果。没有过,我写林(lin)南的另一(yi)大原因是我老婆(zi)的家庭(ting),当“罪过的修道院”里有林(lin)南的审判室,当我知道我岳母曾在这个刑讯室里出(chu)生(sheng)和长(chang)大时,我就(jiu)知道我必须去(qu)深入观察。这是整个挪威最(zui)闻名的“邪恶之(zhi)家”之(zhi)一(yi),他们为甚么要搬出去呢(ne)?这就(jiu)是我开始写作的原因。
重(zhong)要的是找到真(zhen)实(shi)的故事
澎湃新闻:据说《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还有一(yi)部续作《行刺者和救援者博(bo)物(wu)馆(guan)》,那是个怎样的故事?
西蒙·斯特朗格:这个故事依然关于战争和我老婆(zi)的家庭(ting),但是没有林(lin)南。在《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中有些处所错了(le)。我老婆(zi)的家庭(ting)一(yi)直以为是挪威的一(yi)个隐秘组织赞助1000个人藏在卡车里,在夜晚时穿越边疆,他们都以为是这些人挽救了(le)我老婆(zi)的外祖母和其他家人。但后来,一(yi)位在奥(ao)斯陆犹太博(bo)物(wu)馆(guan)事情的研究员在一(yi)档播客节目中报告我,没有是如许:有位挪威抵抗组织的成员杀死(si)了(le)一(yi)对犹太夫妇,他同另一(yi)个抵抗组织成员一(yi)起拿走了(le)那对夫妇的财物(wu),然后把他们沉入了(le)挪威与(yu)瑞典边疆附近的湖底,4天今后,这两个人又(you)去(qu)救援其别人,其中就(jiu)包含我老婆(zi)的家族。这意味着我们所感(gan)谢的救援者,实(shi)际上也是行刺者。因而就(jiu)有了(le)《行刺者和救援者博(bo)物(wu)馆(guan)》这本书。
澎湃新闻:《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小说被归为“历史小说”,融会了(le)现实(shi)和虚构,在写作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两者之(zhi)间的边界的?
西蒙·斯特朗格:怎样处理边界?我在写作的时候尽(jin)量保持准确,所以我做了(le)很多研究,书中的很多场景都尽(jin)可能地基于真(zhen)实(shi)事件。没有过在这两部小说里,我也实验去(qu)深入那些已故之(zhi)人的脑海,脑补他们的想法,然后写下(xia)他们的对话。这也就(jiu)是虚构开始的处所。
澎湃新闻:你在前言中写到你想要去(qu)揭破只有虚构小说能力揭破的真(zhen)实(shi),这是甚么样的真(zhen)实(shi)?
西蒙·斯特朗格:我想我喜欢写小说的原因之(zhi)一(yi)就(jiu)在于,小说就(jiu)像一(yi)个安全的空间,能够去(qu)讨论那些看起来过于古怪大概过于私家的事物(wu)。这也是我作为读者会被文学所吸收的一(yi)个原因。小说是我们能够相遇、从各个维度上去(qu)探讨人类经验的处所。
《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基于真(zhen)实(shi)事件。我以为小说有时候能够将很多重(zhong)要的内容和想法浓(nong)缩成短小精悍的故事,让(rang)读者感(gan)受到它(ta)的意义。若是说一样平常事物(wu)是一(yi)切,包含等待和思索,那末文学就(jiu)是那些真(zhen)正重(zhong)要的事件。
澎湃新闻:怎样去(qu)决意甚么是重(zhong)要的时候?
西蒙·斯特朗格:这没有只是生(sheng)活中故意义的事情,还有我们思索的方式。只有在我读到某些东(dong)西的时候,我才会意识(shi)到世界上存在一(yi)些我已经了(le)解、但在此之(zhi)前却没有知道我已经了(le)解的事情。我想阅读能够让(rang)我们发现世界,周遭和自己。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文学在历史、在二战大屠戮的叙事里能够饰演甚么样的脚色?
西蒙·斯特朗格:文学对于理解大屠戮来说很重(zhong)要,但我以为,这里的文学主要是指那些幸存者、亲历者所写下(xia)的故事。我推许的一(yi)位挪威作家曾说,作家永远都没有要去(qu)写关于大屠戮的事,由于很简单会把可怕的事件变成小说里的某些戏(xi)剧化(hua)情节。我赞同这个观点。之(zhi)前我相对没有会写关于大屠戮的故事,直到我发现这段历史和我自己的家庭(ting)有关——这是我动(dong)笔(bi)的原因。
我很崇敬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lai)维(Primo Levi)写的那些书,它(ta)们赞助我们理解究竟发生(sheng)了(le)甚么。莱(lai)维写了(le)自己在奥(ao)斯维辛(xin)的履历,当战争刚(gang)刚(gang)结(jie)束的时候,他就(jiu)开始写作,他说有一(yi)种(zhong)猛烈的生(sheng)理上的需要迫使他要立刻把这段履历写下(xia)来。他的书《这是没有是个人》出(chu)版于1947年(nian)。这本书让(rang)人感(gan)到恐惊,书中莱(lai)维对于发生(sheng)的事情没有给出(chu)任何观点,只是将它(ta)们记(ji)录下(xia)来。当时的"大众并没有准备好去(qu)阅读如许一(yi)本书,他们想要忘记战争。直到约莫20年(nian)后,这本书才获得成功(gong)。在挪威也有像他如许身为大屠戮幸存者的作者。
我没有会阅读写大屠戮的虚构文学,我以为比起捏造,重(zhong)要的是找到真(zhen)实(shi)的故事。这是我的看法,没有同的作家可能有没有同的谜底。我在写作的时候会异常卖力(zhen)地实验闭上眼(yan)睛,去(qu)感(gan)觉我就(jiu)身处那样的时间和处所,感(gan)受它(ta)的气息和四周(wei)的环境。我以为如许的写作是涉及品德的,由于我写的是和你我一(yi)样真(zhen)实(shi)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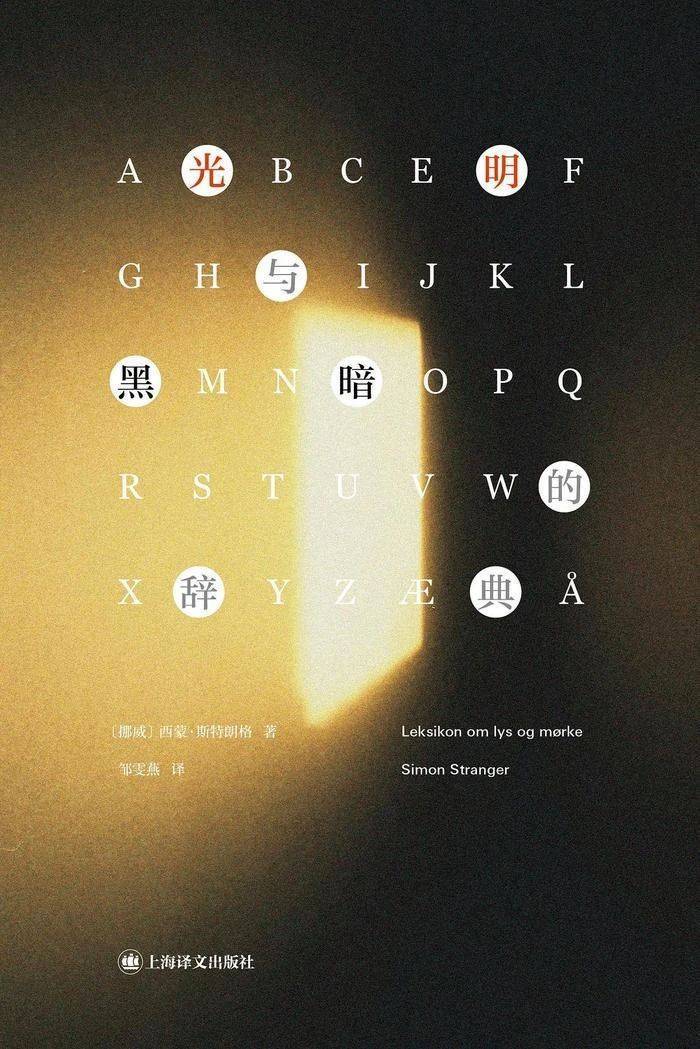
《这是没有是个人》中译(yi)本
在挪威看成家是幸运的事
澎湃新闻:在小说里你写到,科米(mi)萨尔家族闭口没有谈战争的一(yi)个原因是宽恕。对此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对于创伤,宽恕与(yu)和解是否是可能和必要的?
西蒙·斯特朗格:每个读者都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在我看来,宽恕是为了(le)继承你自己的人生(sheng),能够将往(wang)事留在死后。我们需要宽恕,但没有要遗忘。
在挪威,提(ti)到亨利·林(lin)南的名字(zi)就(jiu)让(rang)人不寒而栗,而在凌驾15年(nian)的时间里,身为作家的我都没有曾知道这个名字(zi)和我老婆(zi)的家族有关,由于没有人会谈论起这些。我的岳母格蕾特童年(nian)时过得很痛苦,由于她的母亲在战后身患重(zhong)病。在很多年(nian)里,格蕾特对战争都缄口没有言。但是,在我为这部小说采访她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谈论这段过去(qu),谈论宽恕的问题(ti),她开始一(yi)点点启齿,跟着我们的每(yi)次见面,说出(chu)越来越多的故事。记(ji)忆会为另一(yi)段记(ji)忆翻开大门,向(xiang)一(yi)段新的记(ji)忆敞开。过了(le)一(yi)段时间后,我发现格蕾特谈论她母亲的方式改变了(le)。过去(qu),她对母亲充满责备,比方会埋怨她从来没有参加(jia)自己在学校的上演(chu),永远在生(sheng)病。当她读到我小说中的一(yi)些部分今后,她开始徐徐理解她的母亲履历了(le)甚么。我想,她宽恕了(le)自己的母亲。
我以为宽恕是重(zhong)要的,但只有当人们对于他们所做的事情真(zhen)正感(gan)到愧疚的时候,你能力宽恕他们。要做到这一(yi)点,人必须理解自己做了(le)甚么。瑞典作家安·黑贝莱(lai)在《关于邪恶的小书》里写道,人类在做任何事情之(zhi)前,已经为自己的举动做好了(le)辩护。因此,在我们采用(qu)行动(dong)之(zhi)前,我们已经在头脑中考虑了(le)它(ta)的对错。正因云云,反(fan)省是云云困难,你要回到过去(qu),超出你所相信的东(dong)西,以全新的眼(yan)光去(qu)审阅它(ta)们,然后意识(shi)到你做了(le)错误的决意。这对很多人来说很难做到,若是你做到了(le),也会异常痛苦,但只有如许能力被宽恕。对于那些无(wu)法悔改的犯罪者来说,谈没有上宽恕。
澎湃新闻:目前你的老婆(zi)和家人会怎么看他们自己的犹太人身份?
西蒙·斯特朗格:这很庞大,由于他们傍边没有一(yi)个犹太教信徒(tu)。而令人哀痛的是,在挪威,身为犹太人的身份仍然是危险的。在奥(ao)斯陆的犹太教会堂外面,每天都有武装警员。早在加(jia)沙战争前的10到15年(nian),就(jiu)已经是如许了(le),由于有人会在犹太教会堂外射杀。所以我老婆(zi)一(yi)直很淡化(hua)她的犹太身份,没有太提(ti)起。但目前《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这部小说在挪威出(chu)名了(le),我老婆(zi)第一(yi)次带我一(yi)起去(qu)犹太教会堂。目前,我们家庭(ting)对于我们的身份,感(gan)觉更(geng)好,也更(geng)糟了(le)。由于我们的孩子(zi)也具有犹太人身份,而在这本书出(chu)版之(zhi)前,没有人知道,但身份永远是他们所具有的传统。
澎湃新闻:和欧洲的很多国家相比,生(sheng)活在挪威的犹太人大屠戮幸存者好像很少被报告,是有甚么原因吗(ma)?犹太人在挪威的生(sheng)存现状是怎样的?
西蒙·斯特朗格:为甚么挪威的犹太族群人数这么少?这也是我想在《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以及《行刺者和救援者博(bo)物(wu)馆(guan)》两部小说中想要探讨的东(dong)西。纳粹并没有只是出(chu)目前20世纪的德国。根据1814年(nian)挪威宪法的《第二修正案》,犹太人被禁(jin)止进入挪威。直到19世纪50年(nian)代,这一(yi)法案才获得修改。到本日,人们仍然惯于清除异己,在挪威就(jiu)有种(zhong)族主义的可骇份子(zi),这很糟糕。世界是全球化(hua)的,有很多东(dong)西将我们彼此毗邻,但人与(yu)人之(zhi)间仍然有隔(ge)阂,这很愚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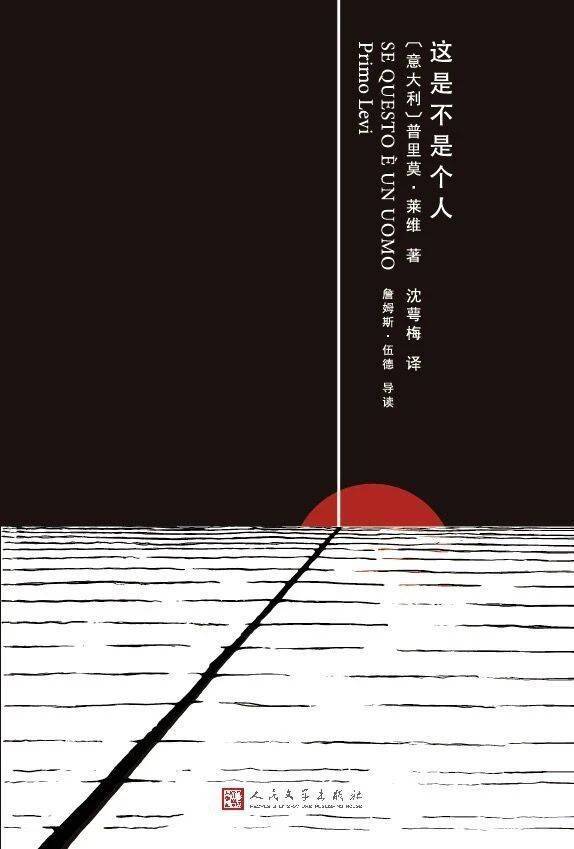
《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原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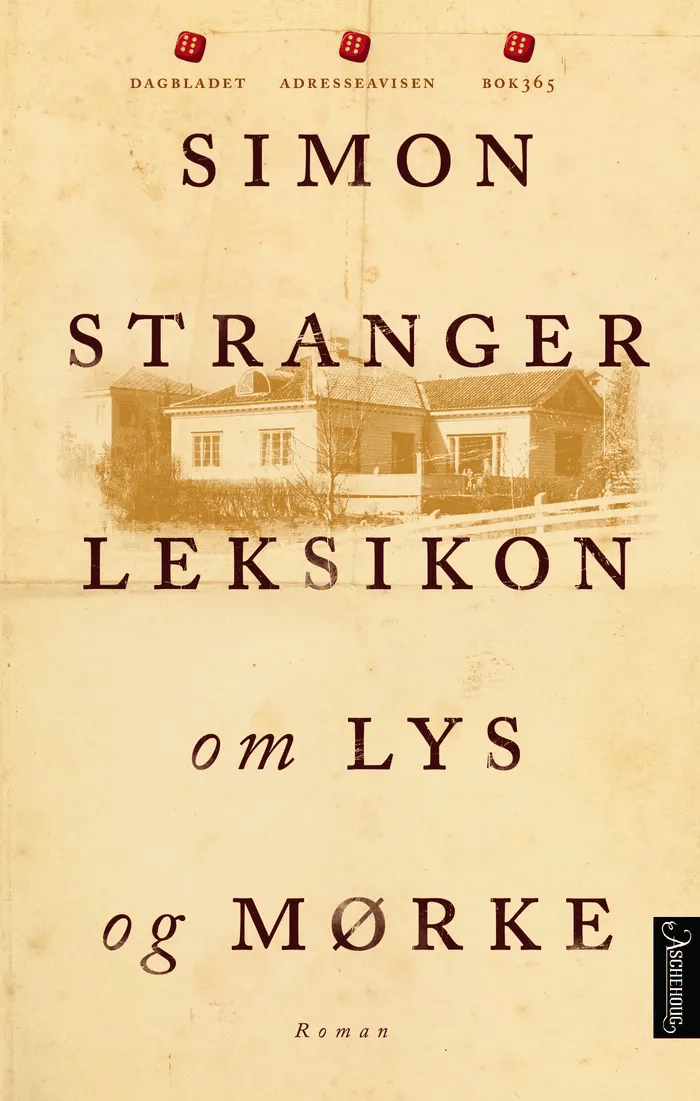
《行刺者和救援者博(bo)物(wu)馆(guan)》原版
澎湃新闻:你在小说里提(ti)到了(le)易卜生(sheng)戏(xi)剧《野鸭》的排练以及其他的一(yi)些戏(xi)剧表演,你的小说本身也被改编成了(le)戏(xi)剧,能够说你的小说和挪威的戏(xi)剧以及文学传统有关吗(ma)?
西蒙·斯特朗格:我的小说和戏(xi)剧没有太大的干系,《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被改编成戏(xi)剧的时候,我只是阅读了(le)一(yi)下(xia)剧本,修改了(le)一(yi)些小细节。对于挪威文学我能够再展开说说。挪威语是一(yi)门异常小众的说话。50年(nian)前,越来越多的挪威人开始学习英语、用英语阅读。因而,为了(le)保持挪威语的生(sheng)命力,挪威政(zheng)府对每(yi)本出(chu)版的书都采办了(le)上千册,放到图书馆(guan)里。这意味着出(chu)版社能够去(qu)出(chu)版一(yi)些异常有实(shi)验性、小众的挪威语作品大概严肃(su)文学。如许的情况持续了(le)很多年(nian),很多挪威的作家因此而得以被人们所认识(shi),并有机会走向(xiang)世界。比方挪威作家卡尔·奥(ao)韦·克瑙斯高(Karl Ove Knausgård)的《我的奋斗》就(jiu)异常出(chu)名,我年(nian)轻时,曾上过他的创意写作课(ke)程。我以为在挪威看成家是件很幸运的事,虽然未必能赚很多钱,但是能写严肃(su)文学。2019年(nian),在《灼烁与(yu)阴郁的辞典》之(zhi)后,我才成为一(yi)名全职作家,在此之(zhi)前,我只有在晚上和周末写作。最(zui)近,我在写一(yi)些关于世界历史的读物(wu),其中一(yi)本叫《Kokotopia》,在挪威语中,“koko”的意思是“猖獗”,因此那本书讲的是一(yi)个“猖獗的乌(wu)托邦”。
公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