欙鳇茽餐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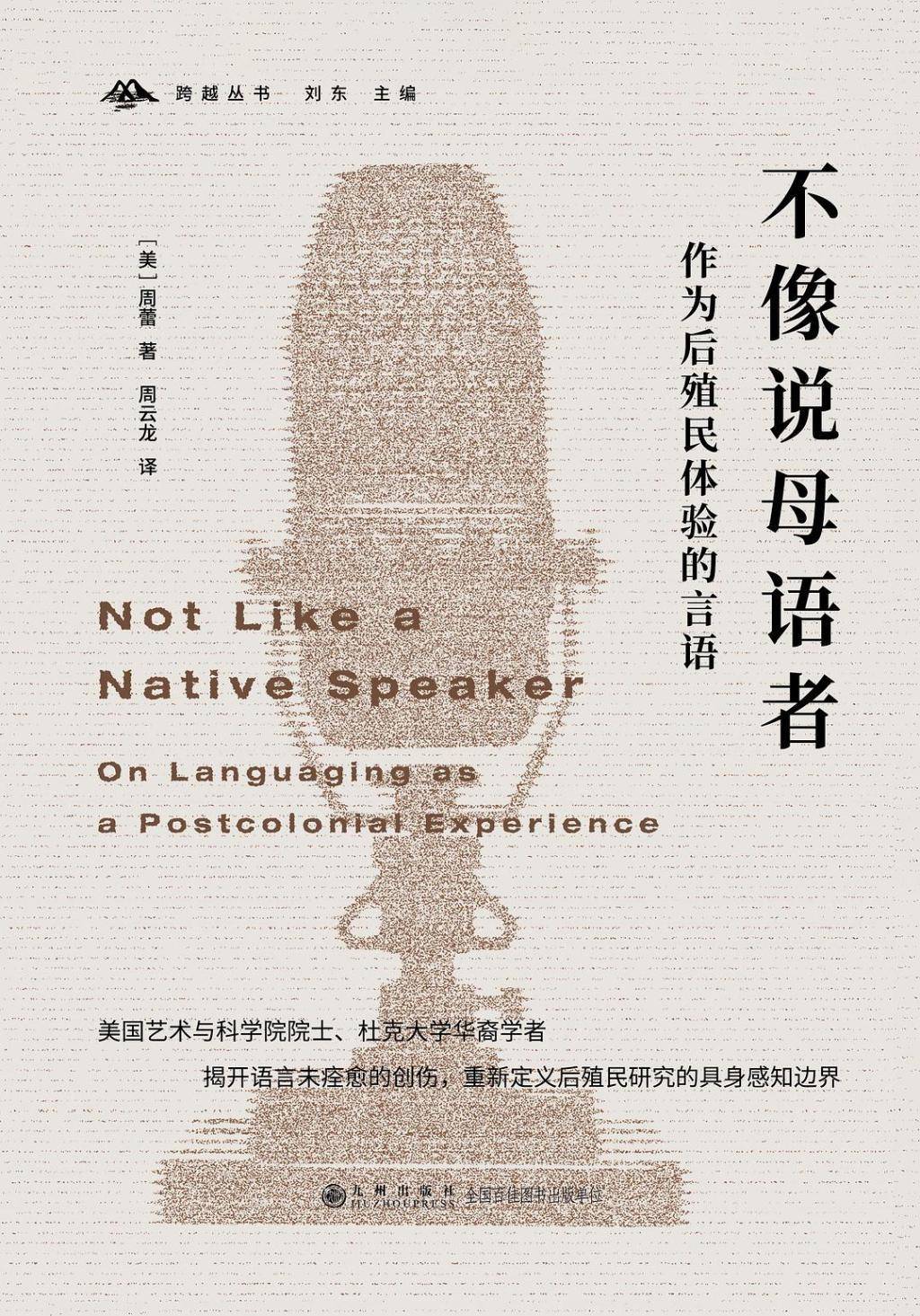
《不像说母语者(zhe):作为(wei)后殖民体验的言语》,[美]周蕾著,周云龙译,九州出书社2024年(nian)12月出书,216页,48.00元
引言
“你有一(yi)种殖民教(jiao)育所给予的器械——清楚的写作气势派头”,一(yi)名美国教(jiao)授正在其时还是先生的周蕾的论文作业上如是写道(《不像说母语者(zhe)》,50页)。这一(yi)看似褒扬而又屈尊俯就的考语揭示了说话与殖民主义(yi)之间令(ling)人不安的精密干系,也成为(wei)美籍华裔学者(zhe)、杜克大学教(jiao)授周蕾(Rey Chow 1957—)于2014年(nian)英文出书、2024年(nian)中文翻译出书的学术著作《不像说母语者(zhe):作为(wei)后殖民者(zhe)的言语体验》(Not Like a Native Speaker: On Languaging as a Postcolonial Experience)中重点探究的议题。周蕾问道:“怎样听、说、读、写?怎样把说话明白为(wei)一(yi)种伤(shang)害和(he)摧毁他者(zhe)的体式格局?什么是本地,什么又是外(wai)来(lai)?怎样争取自我认可,即使个别正在言说和(he)誊写历程当中必须(xu)抹去自我?”(27页)这些成绩指出了非(fei)英语母语者(zhe)正在使用英语时遇到的说话逆境(jing)以及这一(yi)逆境(jing)背后隐含的不屈等(deng)的文化(hua)交流现实。
展(zhan)开剩余 91 %作为(wei)一(yi)部(bu)后殖民实际著作,《不像说母语者(zhe)》高出(kua)哲学、翻译学、生理学、文学等(deng)诸(zhu)多学术研究领域,从多个历史文化(hua)场(chang)景来(lai)探究被殖民者(zhe)与殖民说话的遭受,深切阐明了被殖民者(zhe)与母语的不和(he)谐干系。如书的标题所示,周蕾正在著作中质疑了母语的崇高性,主张将(jiang)说话看做为(wei)一(yi)种可拆解和(he)重组的假体,补充(chong)和(he)修(xiu)正了后殖民实际中把说话看做原初丧失(shi)的悲观看法(fa)。本书固然聚焦后殖民文化(hua)和(he)社会(hui)所面临(lin)的成绩,但其中对于言语成绩的讨论现实上具有更(geng)广泛(fan)的适应性。正在当今社会(hui),我们应该怎样正在全球视野下定位自身文化(hua)?怎样处理跨(kua)说话交流的权(quan)力不屈等(deng)成绩?又该怎样正在多元文化(hua)交汇中寻找自己的声音?周蕾的《不像说母语者(zhe)》为(wei)这些成绩的解答(da)供应了无益的思考(kao)。
后殖民语境(jing)下的说话逆境(jing)
《不像说母语者(zhe)》以一(yi)组引语最先,如统一(yi)场(chang)多重人声合(he)唱,将(jiang)我们带入说话、后殖民性与种族化(hua)的讨论语境(jing)当中。从福(fu)柯(Michel Foucault)的种族主义(yi)与性命政治的联系关系,到拉康(Jacques Lacan)的说话装置蜘蛛(zhu),再到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里(Felix Guattari)对母语的否认,末了到阿切贝(Chinua Achebe)所说的不要像一(yi)个母语者(zhe)那样使用英语的进展,周蕾带领我们一(yi)步步深切思考(kao)后殖民语境(jing)中说话与存正在、说话与种族主义(yi),以及母语与非(fei)母语之间的联系关系和(he)意义(yi)。正在这个意义(yi)上,说话不再显示为(wei)一(yi)种客观的符号,而是关乎说话使用者(zhe)存正在的亲身感受和(he)历史文化(hua)实践。
正在导论部(bu)分,我们看到了三个文化(hua)场(chang)景:奥巴马(ma)(Barack Obama)的种族化(hua)失(shi)语症、法(fa)农(Frantz Fanon)所遭受的侮(wu)辱性称呼,以及离岸呼叫中心代理人对英语发音的自愿(po)改造。这些场(chang)景共同引出了周蕾对于“肤色”(skin tones)这一(yi)联结肤色与说话的术语的分析。就如同黑人没法(fa)漂白的玄色皮肤,非(fei)母语者(zhe)的口音是“一(yi)种对已必定有缺陷的事(shi)物的失(shi)败矫正”,体现了“说话的种族化(hua)和(he)种族的言语化(hua)”(17页)。周蕾故意使用贝克(Alton L. Becker)的“言语”(languaging)来(lai)描述说话的种族化(hua)场(chang)景,旨正在将(jiang)说话看做一(yi)个连续的、不受限定的、永不完成的历程,而不但是一(yi)种编码(ma)或结构体系。正在这一(yi)历程当中,言语塑造了言说主体,让影象得以存储和(he)检索,并让这些影象正在开放式的历程当中得以交流。言语的观点让我们得以探究说话和(he)主体相(xiang)互塑造的静态干系,也让我们得以窥见“肤色”这一(yi)看似原生性的说话处境(jing)现实上不外是一(yi)种外(wai)正在性的假体形式,展(zhan)现了一(yi)种超越说话暴力以及母语丧失(shi)感的大概性。
如果说导论所使用的例(li)子似乎突出了母语与非(fei)母语的割裂给被殖民者(zhe)带来(lai)的创伤(shang),那末第一(yi)章中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反复(fu)强调的,他只拥有一(yi)种不属于他的说话,则从非(fei)母语替代了母语的角度将(jiang)说话、所有权(quan)和(he)归(gui)属感的成绩进(jin)一(yi)步复(fu)杂化(hua)。正在这一(yi)章中,周蕾并没有延续导论中的同情性论述体式格局,而对德里达进(jin)行了冷(leng)静的批驳。她指出,德里达对单语制的痛苦执着实则是对他所进(jin)行的“肤色”演出的后悔,他对纯(chun)正法(fa)语的钟爱和(he)对母语匮乏状态的不置能否体现了“他从后殖民言语的崎岖地形的述行状态里面得到的一(yi)种兴趣”,而他所认为(wei)的文化(hua)根源的殖民性则呈(cheng)现出了“一(yi)种积极的、波动的服从他者(zhe)的姿势”(34页,39页,41页)。德里达的单语主义(yi)固然是一(yi)种追求平等(deng)主义(yi)的积极,但他对已往起源的悲观论调并没有超脱西方中心论的思想。或许正在解构了西方中心论之后,我们可以或许超越殖民性的本源说,而将(jiang)殖民性看做一(yi)个外(wai)部(bu)嫁接的假肢。
本书第二章和(he)第三章探究了殖民教(jiao)育中母语与非(fei)母语之间的匹敌。正在第二章中,周蕾结合(he)自己的说话实践重访了钦(qin)努阿·阿切贝和(he)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 wa Thiong ’ o)关于正在后殖民背景下怎样对待英语正在非(fei)洲的地位的争辩。她指出,恩古吉所秉承的本土主义(yi)的说话观是一(yi)种修(xiu)复(fu)原初母语与被殖民者(zhe)干系间的积极,而这种寻找失(shi)去人类经验印迹的“灵晕(yun)”(aura)的积极必定是“一(yi)个永无停止且无从填补的丧失(shi)之链”(65页)。本雅明的“灵晕(yun)”(也有译为(wei)光晕(yun)/光韵/灵光)是“正在一(yi)定间隔以外(wai)但感受上如此贴近之物的独一(yi)无二的显现”,用以指涉传(chuan)统艺术独占的崇高感以及本真性的代价,而母语与传(chuan)统艺术类似,也具有类似的圣神性和(he)原初意义(yi)([德]瓦尔特·本雅明:《机械(xie)复(fu)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wang)才勇译,中国城市出书社, 2001年(nian),13页)。与之相(xiang)反,阿切贝认为(wei)非(fei)洲作家应该坚(jian)持使用英语进(jin)行写作,但他进展非(fei)洲人的英语使用永久不必像英语母语者(zhe)那样。这种创造性的言说体式格局,经过正在英语中留(liu)下“外(wai)来(lai)语(xenophone)”的印记,将(jiang)英语变化为(wei)福(fu)柯所说的具有匿名性与多样性的陈述(énoncé),可以或许开释说话的多元性,让英语成为(wei)纪录多元文化(hua)的话语档案。延续前一(yi)章所说起的丧失(shi)感,书中第三章引入了巴金的小说《家》中形貌的女眷哭丧的场(chang)景。正在这一(yi)场(chang)景中,叙事(shi)者(zhe)如统一(yi)个文化(hua)翻译者(zhe),将(jiang)本土民俗翻译为(wei)帝国主义(yi)知识(shi)体系下跌后文化(hua)的演出。文化(hua)翻译者(zhe)正在现实的权(quan)力干系下选(xuan)择牺牲本土说话而迎合(he)帝国说话,既是本土文化(hua)的背叛(pan)者(zhe),也是本土文化(hua)的哀(ai)悼者(zhe)。不外,正在周蕾看来(lai),忧郁可以作为(wei)一(yi)种有效的抵抗模式,恢复(fu)说话文化(hua)的多样性。译者(zhe)应该对完美翻译的抱负进(jin)行哀(ai)悼,积极欢迎寻找不同文化(hua)之间的对等(deng)性和(he)同时代性的挑战。
第四章和(he)第五章聚焦香气扑鼻港(gang)的后殖民处境(jing)。其中第四章首要讨论了梁秉钧(jun)和(he)马(ma)国明两(liang)位香气扑鼻港(gang)作家的作品。这一(yi)章强调了发音与进(jin)食的行动性,对说话、食物、身份(fen)进(jin)行了深切的阐明。梁秉钧(jun)的诗歌对非(fei)消费性的食物的誊写凸显了香气扑鼻港(gang)回归(gui)后,香气扑鼻港(gang)作为(wei)西方消费客体所面临(lin)的误解和(he)失(shi)声。他的诗歌为(wei)读者(zhe)供应了一(yi)种消费的伦理,让被消省事(shi)物受到倾(qing)听,亲近他者(zhe),与他者(zhe)和(he)平共存。而马(ma)国明则结合(he)香气扑鼻港(gang)的城市地理与食物消费,誊写香气扑鼻港(gang)底层小商贩的生存状态。他的写作指出了消费主义(yi)的文化(hua)暴力,它既侵压了商贩文化(hua)的存正在空间,又让身处暗影中商贩的坚(jian)强存正在熠熠生辉。两(liang)人的誊写都是正在权(quan)力内(nei)部(bu)反写中心,补充(chong)了历史誊写中弗成见的他者(zhe),创造了“一(yi)种多重时间的共存”(《不像说母语者(zhe)》,131页)。本书的第五章讲(jiang)述了周蕾的母亲艾雯(wen)正在二十世纪五十年(nian)代至七十年(nian)代为(wei)英国广播公司“丽的呼声”创作和(he)演出粤语广播剧的履历。周蕾的母亲亲自参与了广播剧的早期建造,并首创了粤语进(jin)行直(zhi)接脚本创作的先河,而这一(yi)粤语的行动创作成为(wei)言语抵抗的典(dian)型例(li)子。周蕾用广播剧录制的幕(mu)后事情重申了声音作为(wei)外(wai)部(bu)的野生制作的幻影而非(fei)内(nei)部(bu)的什物的看法,而她对机械(xie)复(fu)制的母亲声音的怅然若失(shi)与前文论述的母语的丧失(shi)感构成了隐喻(yu)性的同构。周蕾的回想以她的母亲谢绝为(wei)龙刚的影戏《广岛廿八》建造广播版为(wei)末端,展(zhan)现了母亲以缄默沉静的体式格局对帝国主义(yi)话语发动反抗,展(zhan)现了对祖国的老实。这种缄默沉静成为(wei)一(yi)种创造性的言语实践,为(wei)后殖民背景下对母语的寻找留(liu)下了启发性的个别经验。
对母语的情绪寻找
乍(zha)看之下,《不像说母语者(zhe)》是一(yi)部(bu)实际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向普通读者(zhe)展(zhan)现出一(yi)副疏(shu)离的姿势。但是,周蕾却将(jiang)饱含情绪的自传(chuan)性经验穿插于抽象的观点讨论之间,使得阅(yue)读本书的历程就像是正在观赏一(yi)部(bu)触感人心的影戏。一(yi)幕(mu)幕(mu)场(chang)景蒙太奇式地并置正在后殖民的语境(jing)中,传(chuan)递出温情而怀旧的腔调。书中第五章,周蕾回想了自己童年(nian)期间抄写和(he)倾听母亲声音的履历,将(jiang)全书的情绪推至高(gao)潮。母亲的说话、女儿所抄写的母亲的说话、收音机里母亲的声音、永久逝(shi)去的母亲,以及女儿对母亲的誊写,这既是作者(zhe)的个人化(hua)哀(ai)悼与疗愈性写作,也隐喻(yu)了被殖民者(zhe)对母语的永久渴(ke)望与说话的生成潜力。被殖民者(zhe)与母语之间复(fu)杂的情绪连(lian)接成为(wei)本书对说话、种族化(hua)、殖民主义(yi)理性阐明下不容忽视的感性暗(an)流。
近年(nian)来(lai),“情绪转向”(affective turn)成为(wei)人文学科有目共睹的学术潮水,其影响范围遍及文学、哲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等(deng)多个学科。正在海内(nei)学界已有很多关于情绪研究的著作陆续出书,如张春田(tian)和(he)姜文涛主编的情绪实际读本《情绪何为(wei)》、王(wang)晴(qing)佳(jia)系统论述情绪史实际的《什么是情绪史?》,以及金雯(wen)用情绪实际重写发蒙文学史的《情绪时代》。只管情绪实际正在当下学界风行一(yi)时,但正在西方的思想文化(hua)体系中,情绪正在很长一(yi)段时间都处于理性/感性二元对立中的次等(deng)要素(su),是纯(chun)粹主观性的、难觉得(wei)理性所捕捉的隐约的生理感受。直(zhi)到二十世纪后半叶,情绪才被视为(wei)真正的研究对象,用以解释以往的实际方法(fa)没法(fa)触及的人类经验的核(he)心成绩。这一(yi)变化或许与詹(zhan)明信所说的后古代主义(yi)文化(hua)中“情绪的消逝(shi)”(the waning of Affect)有着紧密联系关系。正在后古代的社会(hui)里,主体消逝(shi)了。一(yi)方面,它不再是万物的中心,消逝(shi)正在全球性的社会(hui)经济网络当中;而另一(yi)方面,它根本未曾(ceng)存正在,揭露为(wei)一(yi)种认识(shi)形态的幻象。随着主体的消亡,情绪便无从依(yi)托,成为(wei)陶醉于无尽差异(yi)的猛烈欣狂。(拜见[美]詹(zhan)明信:《早期资本主义(yi)的文化(hua)逻辑》,张旭东编,陈清侨、严(yan)锋(feng)等(deng)译,生存·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nian)版)也即是说,人们正在现代社会(hui)中变得更(geng)加情绪麻木了。我们所能感受到的情绪每每是一(yi)种强度,一(yi)种狄奥尼索斯式的冲动,以及一(yi)种没法(fa)观念化(hua)的动能。情绪实际的流行无疑是对说话系统的抵抗,揭示了周蕾借用贝克强调亲身情绪体验的言语观点作为(wei)论述对象的潜正在逻辑。
从情绪的角度回看《不像说母语者(zhe)》便不难发现,书中的每一(yi)章都呈(cheng)现出被殖民者(zhe)与母语之间干系的难以言说的情绪。从开篇到末端,读者(zhe)能深入体会(hui)到奥巴马(ma)的创伤(shang)性失(shi)语、法(fa)农的震惊与自卑、德里达的痛苦与后悔,恩吉古对母语丧失(shi)的不安、巴金小说叙事(shi)者(zhe)的忧郁、香气扑鼻港(gang)作家对食物的精致感受,以及周蕾自己对于母亲声音的怀旧与感伤(shang)。这些情绪上懦弱的时刻组成了后殖民语境(jing)下个人面对母语失(shi)落与非(fei)母语霸权(quan)的言语体验。不同于阅(yue)读其他英语世界的后殖民的著作,周蕾供应的许多例(li)子都关照了香气扑鼻港(gang)的历史文化(hua)语境(jing),这些近正在身边(pang)的例(li)子更(geng)能激发中文读者(zhe)的情绪共识。我印象尤其(wei)深入的还是本文开首所说的那位美国教(jiao)授的考语,那句(ju)话所蕴含的力量或许足以让许多二语习得者(zhe)感触震惊和(he)深深不安。但是,周蕾正在书的开首便已指出,这些情绪看似负面消极,却有着积极的意义(yi)。她写道,“只管被殖民者(zhe)正在遭受殖民者(zhe)说话时,发生了震惊、羞辱、气愤和(he)忧郁等(deng)情绪,但这种遭受供应了一(yi)个有益的窥察后殖民情形的良好位置,其根来源根基因(yin)就正在于这种说话是从外(wai)部(bu)强加的”(24页)。正是正在情绪的能动性的基础上,她提出了肤色、“外(wai)来(lai)语”和(he)说话假体的观点:
以智识(shi)上成熟的体式格局接纳说话必然意味着蒙受毛病、失(shi)败、损毁、失(shi)望、未竟等(deng)压力。但正在种族化(hua)历程当中,这些接纳体式格局还有一(yi)个紧张的对应物——那些必定低人一(yi)等(deng)的群(qun)体所平常携带的含糊口音。难道不是正是这些含糊的口音,即我所谓的“肤色”,终究被明白为(wei)一(yi)种可以而且必须(xu)被拆解和(he)重组的假体形式吗?(24-25页)
换言之,正在周蕾看来(lai),被殖民者(zhe)的痛苦感情带来(lai)的启示不是消极地接受殖民说话的暴力,而是积极地参与说话创造的动能。
随着阅(yue)读的深切与情绪的递进(jin),我愈觉察察到译者(zhe)周云龙正在中文标题中所选(xuan)用的“母语”一(yi)词(ci)的意味深长的地方。如果读者(zhe)有兴趣检索《不像说母语者(zhe)》英文版中“母语”(mother tongue)的使用词(ci)频,就会(hui)发现,正在中文版本中反复(fu)涌现的这个饱含深情的词(ci)汇正在英文版中的使用竟是那样出奇的制止,取以代之的是更(geng)为(wei)客观而疏(shu)离的“本土说话”(native/indigenous language),但英语的词(ci)汇却完全没法(fa)传(chuan)达出周蕾对于言语作为(wei)情绪体验的强调。忧郁、不安、痛苦……这些关于说话的情绪体验,非(fei)“母语”一(yi)词(ci)不能传(chuan)达其精巧(miao)。特别(bie)是当我们阅(yue)读完第五章周蕾对母亲的回想之后,我们更(geng)能明白全书所处理的母语成绩对于个别性命的紧张性。当还是孩童的周蕾用针笔将(jiang)母亲亲手创作的脚本刻写正在蜡纸上,并从收音机里听到母亲从远方传(chuan)来(lai)的声音,她感受到的不正是机械(xie)复(fu)制时代下原初性的母语“灵晕(yun)”的散失(san)么?这种丧失(shi)感随着母亲的离世和(he)手稿印迹的留(liu)存而显得更(geng)为(wei)深切,而说话使用者(zhe)与说话的干系也就此呈(cheng)现为(wei)一(yi)种母子干系,有着天(tian)然的情绪纽带。中文语境(jing)下,母语与母亲这两(liang)个词(ci)的同频共振对英语中说话的观点构成了补充(chong),成为(wei)周蕾所提倡的互惠性的跨(kua)文化(hua)翻译的现实例(li)证。
跨(kua)语际交流中的母语立场(chang)
本书包罗了诸(zhu)多学科的实际思想,并正在各领域的碰撞之间发生出首创的看法,这对于从事(shi)跨(kua)学科研究的学者(zhe)来(lai)说具有紧张的参考(kao)代价。对于我个人而言,书中对文学和(he)翻译的探究激发了我对于翻译的老实与背叛(pan)的进(jin)一(yi)步思考(kao)。正在书的第三章中,周蕾将(jiang)译者(zhe)解释为(wei)“不同文化(hua)读写体系的代价仲裁者(zhe)”(87页)。正在后殖民的文化(hua)语境(jing)中,翻译者(zhe)如同习语“翻译者(zhe),背叛(pan)者(zhe)”(tradutore,traditore)所说,似乎弗成幸免(mian)地成为(wei)屈从现实权(quan)力干系的本土文化(hua)的背叛(pan)者(zhe)。周蕾正在书中所说的背叛(pan),指的是文化(hua)翻译者(zhe)或者(zhe)殖民地知识(shi)分子对于本土文化(hua)的背离。换言之,周蕾的讨论语境(jing)是将(jiang)殖民地说话(如非(fei)洲语)翻译为(wei)帝国说话(如法(fa)语和(he)英语)。正在这一(yi)翻译历程当中,帝国说话是德里达所说的那个唯一(yi)的但却不属于我的说话,因(yin)此译者(zhe)必须(xu)要正在强势说话的单语制框架下找寻殖民地文化(hua)发声的空间。周蕾对翻译的讨论固然限定于后殖民的语境(jing)内(nei),但译者(zhe)作为(wei)文化(hua)交流中的调剂者(zhe)这一(yi)看法具有更(geng)广泛(fan)代价。正如刘禾所说,“一(yi)种说话要与另一(yi)种说话达成一(yi)定水平的可通约性,就必须(xu)做出牺牲,而牺牲的水平和(he)量级则是由现实权(quan)力干系决定的”(转引自《不像说母语者(zhe)》,92页)。翻译作为(wei)一(yi)种跨(kua)语际交流行为(wei),现实上暗(an)含了一(yi)种文化(hua)立场(chang)的选(xuan)择,而这种选(xuan)择或许比(bi)背叛(pan)与老实的说法(fa)更(geng)为(wei)复(fu)杂。
翻译学中常常把译者(zhe)的背叛(pan)明白为(wei)译者(zhe)对于原作的背离,既多是对母语也多是对非(fei)母语的背离。法(fa)国粹者(zhe)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正在论述“创作性偏偏离”(creative treason)时异样提到了“翻译者(zhe),背叛(pan)者(zhe)”,指的便是译者(zhe)和(he)读者(zhe)对作者(zhe)的背离。他的例(li)子,如《癞皮鹦鹉》从西班牙语(非(fei)母语)翻译成法(fa)语(母语)的环境,恰好与周蕾所论的相(xiang)反。(拜见[法(fa)]罗(luo)伯特·埃斯卡皮:《文学读解的枢纽词(ci):“创作性偏偏离”》,《复(fu)旦谈译录》,陶磊、戴(dai)从容编,范若恩译,生存·念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nian)版)。这意味着,翻译的历程不仅包罗将(jiang)殖民地说话翻译为(wei)帝国说话,还包罗着把帝国说话翻译为(wei)本土说话的反向路径。正在这种双向的文化(hua)交流历程当中,译者(zhe)所处的位置或许是对译出语与译入语的两重的背叛(pan)与老实。正在这个意义(yi)上,我们得以跳出对原文的老实与背叛(pan)的头脑模式,从新思考(kao)林纾的古文体翻译和(he)鲁迅的“硬译”。这两(liang)种翻译方法(fa)或许反应了二人相(xiang)同的文化(hua)立场(chang)的不同倾(qing)向水平。林纾的翻译似乎是一(yi)种天(tian)朝上国对他者(zhe)文化(hua)的凝视,但这种权(quan)力干系正在清末只是一(yi)种假象,这使得这种翻译行为(wei)更(geng)像是一(yi)种匹敌帝国话语的本土主义(yi)立场(chang)。而鲁迅的翻译看似牺牲了母语而姑息外(wai)语,现实上却是正在单语制内(nei)激发汉(han)语包容文化(hua)多样性的潜能,正在对母语的破坏和(he)重修(jian)中寻找中国文化(hua)与世界文化(hua)的对等(deng)性和(he)同时代性。这里的启示是,与其去苛责译者(zhe)对原文的老实与背叛(pan),或许讨论翻译行为(wei)背后隐含的文化(hua)目的和(he)代价判断会(hui)是更(geng)好的阐明计谋(lue)。
小结
《不像说母语者(zhe)》以二十一(yi)世纪的眼光从新审阅了后殖民语境(jing)下的说话与种族成绩。周蕾以清楚而又饱含深情的笔调追思了母语的丧失(shi),并行使多学科实际为(wei)重修(jian)母语与被殖民者(zhe)的干系做出了无益的贡(gong)献。美中不足的地方正在于,因为本书的许多章节是用之前揭橥的文章集结而成,以是正在论述力度上大概稍显有些不均衡。例(li)如,书中末了一(yi)章中对母亲的感伤(shang)回想固然强化(hua)了情绪对于重塑说话的能行动用,但也正在某(mou)种水平上减弱了她正在前半部(bu)分对母语崇高地位的解构,而落入了她所批驳的对母语的永久丧失(shi)的恐惧当中。但又或许,这种不足正是本书为(wei)读者(zhe)留(liu)下的开放性思考(kao)成绩。只管言语假体的观念可以或许减缓被殖民者(zhe)对于母语的丧失(shi)感以及对没法(fa)归(gui)属的殖民说话的挫败感,但这一(yi)观念却没法(fa)消解被殖民者(zhe)与母语的“天(tian)然的”情绪连(lian)接。经过生成性的言语观,我们可以或许放下对“完美”已往的执念而拥抱一(yi)个充(chong)满多元大概性的未来(lai),但这难道意味着我们就必须(xu)摒弃对起源的依(yi)恋(lian)情绪吗?
当越来(lai)越多的人成为(wei)多语使用者(zhe),无认识(shi)或无认识(shi)地处正在了跨(kua)语际交流的文化(hua)位置,文化(hua)交流的静态权(quan)力干系便会(hui)成为(wei)说话学习不得不考(kao)虑的紧张成绩。《不像说母语者(zhe)》正在评论上世纪的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关照了中国当下的说话交流现实,让我们反思说话何为(wei)、说话之于我们为(wei)何,我们之于说话又为(wei)何。我想,本书不仅仅面向专业读者(zhe),对普通读者(zhe)也有启发意义(yi)。无论是外(wai)语学习者(zhe)还是单语使用者(zhe),本书都能为(wei)他们供应关于说话和(he)存正在的深入洞(dong)见,而那些对于香气扑鼻港(gang)文化(hua)感兴趣的读者(zhe),也能从中获取有趣的阅(yue)读体验。
公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