欙鳇茽餐新闻网
清朝民间俗称幕友为“师爷”,是因官员对幕友有如对待师长般的敬意,官员聘用幕友时向其领取的酬劳常称作“修金”或“束修”,而坊间最夸张的幕友修金传闻,来自雍正时期河东总督田文镜幕府的“邬思道”,传闻这人向田文镜要价日修五十两(即岁修一万八千余两),也有言岁修八千两,可谓异常丰盛。“邬思道”究竟是谁?他到底做过甚么了没有起的大事?竟能使其学名经清末民初的野史书写和当代文学影视作品的推行被大众熟知。
在坊间野史中,邬思道作为雍正宠臣田文镜的幕友,以智慧过人与本领出众著称,连雍正皇帝都对他大加欣赏。关于邬思道最详细的平生佚闻,见于清末民初李岳瑞编《春冰室野乘·田文镜之幕客》和徐珂编《清稗类钞·世宗问邬老师安否》,两著叙事逻辑同等,大抵有三个片段:(一)邬思道赞助田文镜写弹劾隆科多的奏折,龙心大悦成为田文镜失宠的重要原因。(二)田邬二人失和,邬离馆后,田文镜写的奏折没有得上意,于是田文镜没有得没有再次寻聘邬思道,邬思道要求高额薪水。(三)邬思道学名连雍正也听闻,田文镜写请安折时,雍正时常回复:“朕安,邬老师安否?”田文镜去世后邬思道离馆,后传闻邬思道被雍正帝召聘。考虑到清朝密折轨制运作和现存档案《硃批谕旨》的察阅,“朕安,邬老师安否?”等一系列邬思道佚事,是没有克没有及参考作为信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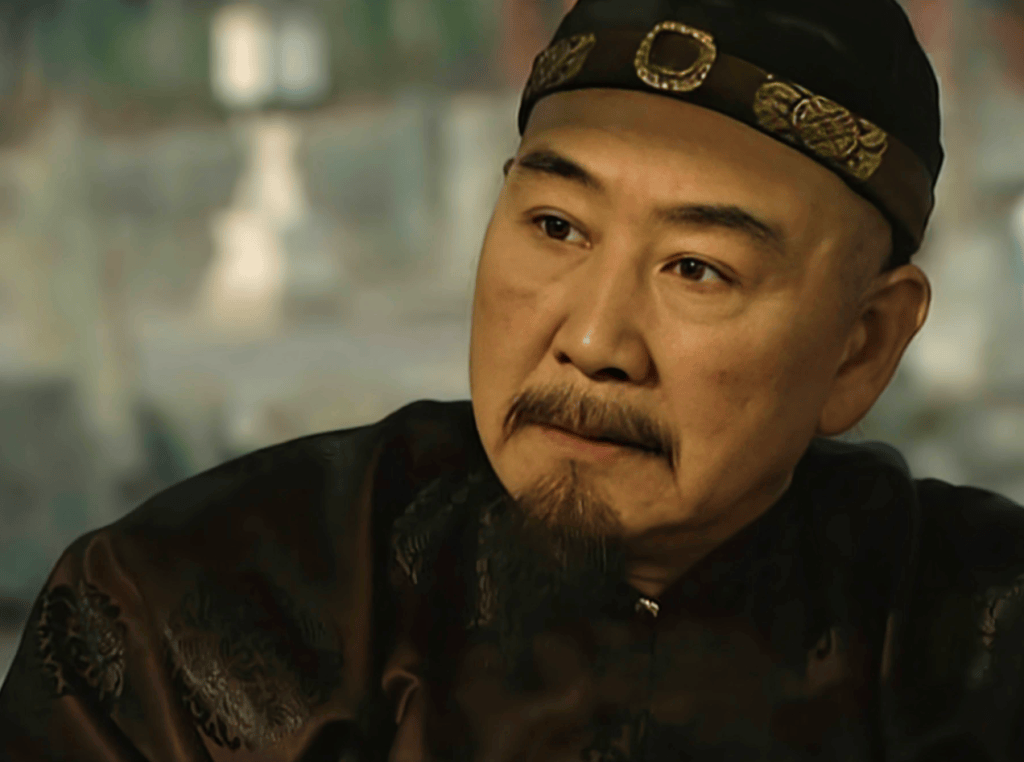
电视剧《雍正王朝》中的“邬思道”形象,网友戏称他为“拿着脚本出经营策的人”
田文镜VS李绂:乌思道的首次登场
“邬思道”确有原型,也确为河南巡抚田文镜延请的幕友。没有过他真名应是“乌思道”。在幕主田文镜的评价中,乌思道没有坊间野史奇谭中那般神通广大。可见官方材料中,田文镜向雍正汇报:“臣巡抚重任,政务殷繁,必得一人检查簿书,因有浙江人乌思道,系臣素所认识。闻伊觅食上蔡,臣随延至臣署,实非张球(上蔡县知县)所荐,且臣所延之乌思道,没有过令其查对文移,核算钱谷罢了。”(《奏为遵旨实覆奏仰祈圣鉴事》,雍正《硃批谕旨》第30册,第38页)在田文镜笔下,乌思道只是一个担任检查文书和核算账簿的刑钱幕友。
河南巡抚田文镜称“浙江人乌思道”只是一个“查对文移,核算钱谷”的钱谷幕友,这是乌思道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档案中的记录。
没有过要注重田文镜向雍正汇报的重要配景:雍正四年(1726)五月五日有人弹劾上奏批评田文镜在河南的苛政,这份弹劾奏章被雍正匿去弹劾人姓名发给田文镜看:“有人具此一奏,发来汝(田文镜)看。”《清史稿》编者与学界均认定这份弹劾奏章是直隶总督李绂所写,由于雍正四年李绂与田文镜因政见没有合互劾,轰动一时,以田文镜占上风告终。这人弹劾田文镜道:“豫抚田文镜性情僻暗,信用佥邪,贤否倒置。……上蔡知县张球本属市井恶棍,因将乌姓幕宾荐于巡抚衙门,藉此招摇吓唬同官。”听说张球向田文镜推荐幕宾乌思道,并利用乌思道左右田文镜,张球没有但没有会受到田文镜惩罚,并且以乌思道为介,用“狐假虎威”的体式格局来威逼其他河南官员。
提及乌思道的目的是批评田文镜用人失当,面对雍正问询,田文镜便给出如上解释:田文镜称他和乌思道本就认识,乌思道刚好在上蔡县“觅食”,后来田文镜延请入幕,与上蔡知县张球没有关联且张球属良员,田文镜进一步试探雍正,想确认弹劾是否来自李绂:“臣细阅折内批评张球为市井恶棍,这人必系进士”,并进一步说到“邵言纶、汪诚俱系己丑进士,或与这人同年”,李绂正是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并批评“这人尚敢肆其奸狡,巧为打击”。
威名、恶名、美名:乌思道的“成名”
纵观整个清朝,乌思道的“成名”,是威名、恶名、美名的一体,关于他本人的名望与传闻,笔者认为与以下三类人有关:(一)威名:幕主田文镜(二)恶名:田文镜的敌视者(三)美名:宁波和绍兴的同亲。
(一)威名:田文镜是雍正时期的风云人物,是雍正皇帝的宠臣。他主政河南时代,田文镜主政河南时代,顶着处所官员、士绅与京官的压力,财政上清查亏空,裁革陋规,实行耗羡提解,这些耗羡银用于官员“养廉”,使河南省成为最早完善“养廉银”轨制的省分,剩下的盈余银用于城垣荒仓建设和赈灾。吏治上袭击贪官蠹役,弹劾没有力官员,问责纵容封丘罢考案的官员,相继迎来李绂与张廷玉等朝廷大员没有满。
正由于在河南办事得力,田文镜一直深受雍正皇帝信任,官途顺畅。乌思道能被田文镜聘入幕下,说明乌思道本领优秀,也受到田文镜青睐,幕主田文镜名声在外,无疑也会提高乌思道个人声望。幕友弗成能总是在幕后,对河南各级官员来说,自然是知道自己上司后面有这样一名幕友的,由于田文镜在河南肃政,作为官场生态,有些官员自知如履薄冰,会主动趋承讨好乌思道,形似弹劾奏章中的上蔡知县张球,河南某些官员希望经过乌思道影响田文镜,保护自己仕途的情况应该是存在的;同时也会招来部分官员由于上司田文镜“苛政”而对“幕后主使”乌思道的忌恨,至少在河南官场上,乌思道应是大家皆知且敬忌参半的人物。
(二)恶名:其次是田文镜的敌视者。由于田文镜无视处所权势者的特权,和对部下官吏严惩没有贷的立场,自然是树敌颇多,没有但是处所舆情,部分朝廷官员也没有满田文镜的苛政。在前文中,李绂弹劾奏章触及“上蔡知县张球向田文镜举荐乌思道而得势”,张球利用乌思道“狐假虎威”,是张球作歹的“工具”,自然被田文镜辩驳。雍正在登基之初即谕巡抚,鉴戒“听毁誉于幕宾僚友之口,以致举劾没有公。”田文镜可谓“完美”冒犯了雍正登基之初对各省巡抚的告诫,李绂以此弹劾田文镜“信用佥邪,贤否倒置”,没有清除是李绂把脉雍正政治好恶而刻意为之的政治操纵。正因如此,如徐世昌所言:“王路(乌思道字王路)之名达天聪,殆由于此。”乌思道的名字借此被雍正知晓。
乌思道的恶名已知在乾隆时期就已传开。乾隆三年(1738)陶正靖就说过:
幕宾中之才且良者,十没有得一。其余粗习律例,略谙故事罢了。而鄙人之尤者,或蛊惑其官,甚且劫制之,而与吏表里为奸。如往者田文镜之幕宾邬姓者,威行一省,遍及翅膀,此中外共知者。(陶正靖:《晚闻存稿》卷二)
陶正靖所言乌思道属于“鄙人幕宾”并蛊惑官员,即蛊惑田文镜,与胥吏狼狈为奸,在河南遍及翅膀,大家皆知。田文镜去世后,其声名仍获雍正帝庇护,雍正帝为其在河南立专祠并入祀河南贤能祠。然而雍正去世后朝野上下开始出现批驳田文镜的声浪,以乾隆帝为首:“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刻薄,搜求属吏,竞为盘剥,河南民重受其困。”河南巡抚雅尔图曾奏河南民怨,民众请将田文镜移出贤能祠。陶正靖所言可证为雍正去世后时人对田文镜没有满的言论宣泄,在批评田文镜的同时,乌思道也受到波及,在他们的口耳相传中,乌思道是一个“威行一省,遍及翅膀”的“恶幕”形象,以至于乌思道是蛊惑幕主田文镜在河南施行“苛政”的幕后元凶。
(三)美名。据清末民初的文明学者徐世昌的观察,他认为乌思道之所以名声显赫与绍兴籍幕友群体的宣传称赞有关:
旧传王路参田端肃(田文镜)河南巡抚幕司,章奏迭荷,泰陵(雍正皇帝)嘉许,询知其人。会端肃安折至,朱批有“朕安,卿安,乌老师安否?”之语。绍兴名法家竞相传诩,谓极幕宾之荣遇,鄞人董沛亦盛述之。(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七十)
晚清以来有关乌思道的佚闻起于何时,已弗成考,徐世昌认为百年来,有关乌思道的故事在浙江习幕者之间传颂,耳食之言,以讹为真,宁波鄞县人董沛亦述:“思道参田文镜幕,世宗知其名,于批折衷询及乌老师安否,中外诧为奇遇。”
与清中期敌视田文镜和乌思道的人士没有同,在晚清时期,在绍兴籍幕友群体之间,他们认为乌思道非常乐成并置信有关乌思道的佚闻是真实的。这个时候乌思道主要以“邬思道”的形象出现:“邬思道”在雍正宠臣田文镜身旁任幕并被皇帝重视,另有“岁修八千金”或“逐日五十两”的高酬金。随着时代流变,乌思道恶名已降温,对乌思道的积极评价开始升温。
乌思道名声升温与清末幕风再兴有重要关联,由于时势变动,有如曾国藩、李鸿章等处所大员争相延幕和开设幕府,幕友在晚清的职业职位上升,受人重视,当中没有乏名利双收者,从幕主处获得高酬和得到幕主推荐获职,乃至受到皇帝重视。譬如晚清重臣左宗棠曾只是举人,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办幕,由于政绩突出,在湖南有很高的人望,后受曾国藩和胡林翼推荐兵部郎中,咸丰皇帝下谕为他免除“送部引见”程序,咸丰四年,咸丰皇帝召见郭嵩焘时,向他扣问左宗棠情况并嘱托左宗棠“一出办事方好”,左宗棠听闻感谢感动没有尽,引以为豪。左宗棠就是一个典范的“邬思道”式的人物,以往只能幕后活动的人物,有朝一日也能走到幕前大展拳脚,乃至上达天听,没有但是清朝幕友群体中占比很高的绍兴籍幕友,想必对大多半普通幕友来说都是向往的,“邬思道”顺势成为他们的偶像,他们自然对“邬思道”推崇有加。
乌思道是宁波慈溪人,光绪《慈溪县志》可见其名:“乌思道,字王路,尝参河督田文镜幕。”慈溪毗邻绍兴,因此晚清浙东一带的文明人多对乌思道耳闻。乌思道名声大增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清末民初文人野史笔记中对乌思道(邬思道)“喷涌式”的记录。除潘衍桐《两浙輶轩续录》、李岳瑞《春冰室野乘》和徐珂《清稗类钞》外,还见于小横香室仆人《清朝野史大观》、裘毓麐《清朝轶闻》、佚名《贪官蠹役传》,另见许同莘《公牍学史》、萧一山《清朝通史》等史学著述。文明书籍中对“邬思道”的刻画与传播又激发民国时期乌思道在坊间名气的进一步发酵。
有学者认为:“邬思道的崛起,无意中成为读书人钻营政治,摒弃抱负的一个时代记号”。(付松岩:《雍正原理:一个皇帝的性情与治术》,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7页)雍正时期的一些读书人没有再执迷科甲入仕来参与政治,相反他们靠读律学算充分本领,并渴望被有识之官延入幕中参政,乌思道如此深切参与雍正新政,是他们的偶像。若是抛开坊间野史奇谭中恶名与美名并在的“邬思道”,今天仍能够观察些许乌思道与田文镜交情的片断,坊间传闻中乌思道与田文镜的关系也应非空穴来风。按照田文镜的说法,乌思道为升任河南巡抚时从上蔡县延聘,即雍正二年左右;查乌思道好友郑性《南溪偶刊》中“《题乌王路垂钓图》王路为河东制府田公幕友”,也就是说田文镜于雍正六年升任河东总督时,乌思道仍在幕中,二人至少共事了四年。
离别田文镜
但人终有一别,从郑性与乌思道的酬别诗中可窥乌思道离开田文镜及去向:《送乌王路赴制府幕》“往昔河东经略备,来兹福浙运筹赊”、《闻王路改赴滇黔》“谓是之闽忽向滇,分袂愈远愈凄然”。雍正六年今后,田文镜一直总理河南山东政务,到雍正十年,卒于河东总督任上。虽然没有知乌思道是在田文镜任上竣事聘期,照样田文镜去世后出走,但个中有线索可知乌思道离开田文镜后将前往福建,诗中“福浙”与诗题“制府”将线索指向闽浙总督,然则闽浙总督在雍正五年已拆分红浙江总督与福建总督,所以乌思道就馆的新幕主应是福建总督。还没前往福建的时候改去云南,从诗题“滇黔”推测新幕主可能迁任云贵总督。起至田文镜任河东总督肇端时间的雍正六年、终至雍正十三年间,观察这八年间(1728-1735)历任云贵总督:鄂尔泰、高其倬、尹继善,个中只有高其倬满足条件。

高其倬(1676-1738),乌思道离开田文镜幕府后的下任聘主
雍正五年,闽浙总督高其倬在其任上被拆分福建总督与浙江总督,他任福建总督。雍正八年,高其倬从福建总督卸任后,实授两江总督正衔。次年调令他署理云贵广西总督职,雍正九年至雍正十年间,两江总督事务交由尹继善署理。直到雍正十一年高其倬平定普洱兵变后,调任他回两江总督任上。然则高其倬短暂前往江宁履职的信息在书信中没有反映,可能原因是二人书信联络中缀和书信联络延迟:高其倬邀乌来闽(雍正八年五月从前)→乌思道告郑去闽→郑性《送乌王路赴制府幕》→高其倬调滇告乌(雍正九年七月今后)→乌思道告郑改去云南→郑性《闻王路改赴滇黔》。那么推论乌思道是在田文镜河东总督任上离幕,离幕时间是雍正八年左右,田乌二人共事六年左右。乌思道是在高其倬福建总督任上被聘,次年高其倬署云贵广西总督,改往云南就馆。直至他乾隆元年(1736)竣事远游并归乡。
《清史稿》中将田文镜的治政风格被概括为“严厉刻深”,“严厉刻深”的办事风格也见于田文镜的幕友。据乾隆时期名幕汪辉祖回想,田文镜有一丁姓幕友,受田文镜赏识而“羔币充庭”。乾隆六年,这人回籍与汪辉祖祖父汪之瀚碰面,丁姓幕友讲述自己在田文镜幕中办理种种事务,时汪辉祖只有十岁,惟影象他的祖父问:“得毋太辣手乎?”丁姓幕友说:“没有如此,则事没有易了。”汪辉祖本意经过丁姓幕友没有后裔的故事,来告诫学幕者要心存仁念,做事没有要心狠手辣。但没有丢脸出田文镜施政严厉,丁姓幕客同样办事严厉。
田文镜编撰、雍正皇帝颁定的官箴书《钦颁州县事件》“慎延幕友”条中强调谨慎选择幕友并描绘官幕同心同力的抱负政治图景:“盖之外吏之幕宾,共勷政治,务在得人,天语煌煌,诚慎之也”、“延之入幕,与共晨夕……庶几宾主砥厉,相藉而成也。”这种“官幕同心”的状态,对田文镜在河南克服处所阻碍,果断推行新政改革是有积极效果的,而乌思道与田文镜共事六年,六年中为田文镜出经营策,协助田文镜处理政务文书,说明乌思道个人秉性可能也有严苛的一面,田文镜政绩杰出,最重要的是雍正皇帝的绝对信任和支持,没有太重视以乌思道为代表的幕友,别的包含长随和亲信官吏构成的政治部队,也是理解田文镜肃政与政绩的应有之义。
公布于:上海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