欙鳇茽餐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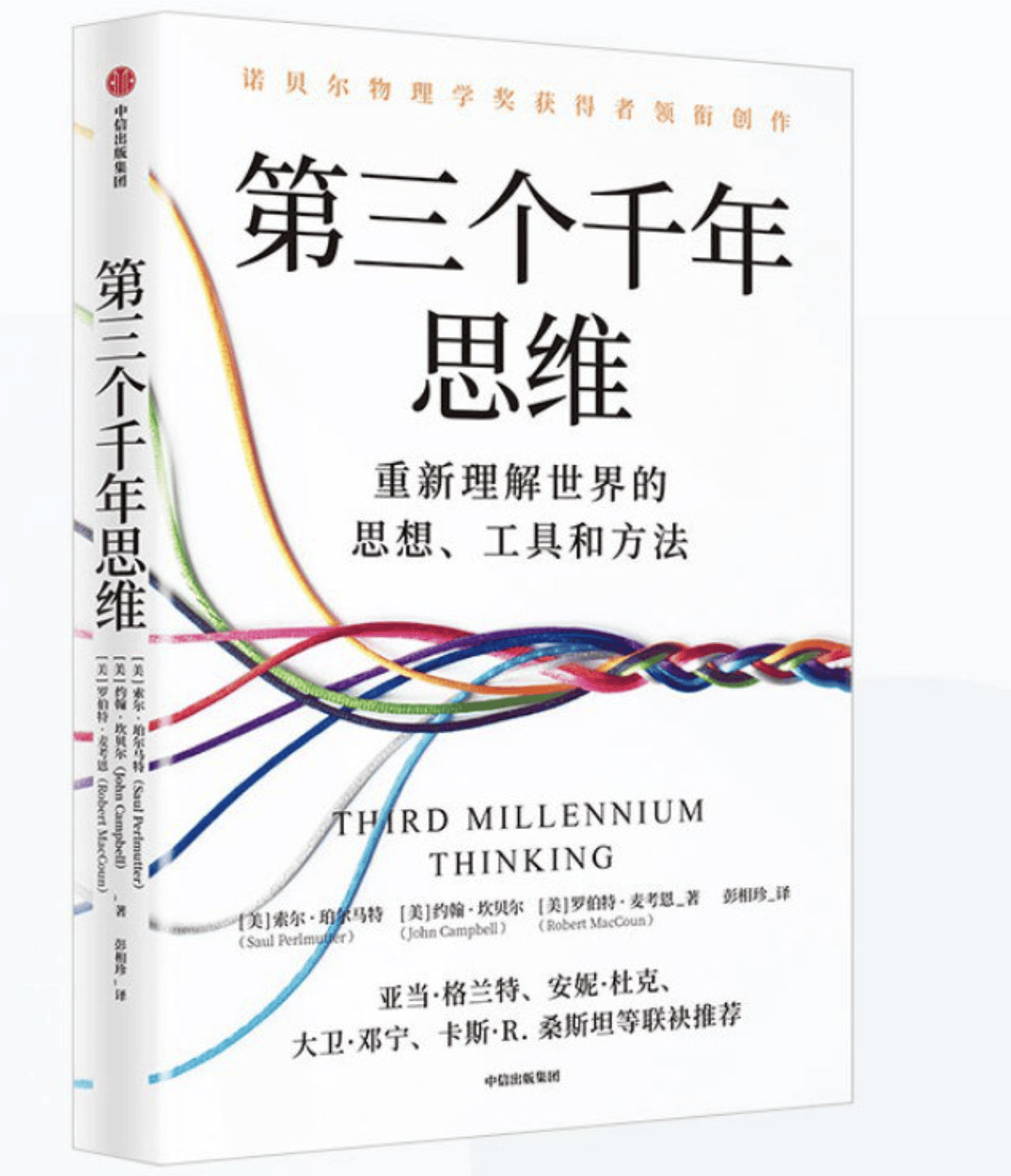
下文经出版社受权摘编自《第三个千年头脑》,作者: [美] 索尔·珀尔马特 等,译者: 彭相真,中信出版社2025年2月。有删节。
回顾技术、医学和科学领域的创新历程,我们或许不难发现,事实上,许多庞大发现和发现并不需要尖端的设备、深奥的数学理论或巨额的资金投入,杠杆、音标、钉子、流水线生产方式及控制实验等都是典型代表。那么,为何它们的问世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举个例子,早在16世纪便有人提出了细菌致病理论,然而直到3个世纪后,法国化学家及微生物学家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和英国流行病学家约翰·斯诺(John Snow)才终究让这一理论得到了重视。鉴于现代人类的大脑形态在人类以文字纪录历史之前便已完成退化,诸多此类创新好像本有可能更早出现。
想象一下,若是一切都从零开始,你还能否搞定需要本日完成的各类事务?你晓得怎么为本身亲手做一双既耐穿又舒适的鞋子吗?你能不能计划出一把牙刷、一副眼镜或者一卷胶带?又或者发现煮过咖啡豆的水竟然能让人保持头脑清醒?孩子们也总会啼笑皆非地问道:手机的大部分基本功效早在去年就更新了,为什么爸妈至今都没有发现呢?
展开剩余 90 %形成这种效果的一大原因是,环境中的许多干扰因素增加了人类从经验中吸收教导的难度。我们的感官不断受到来自方圆环境的多重刺激,然而从第6章介绍的角度来看,个中一些是有用的旌旗灯号,其他则是随机噪声。尽管部分旌旗灯号之间存在联系关系,但我们很难在扑朔迷离的现实天下中探寻它们之间的可靠联系,因为这些联系往往是概率性的(A发生之后,B可能会发生),而非确定性的(若是A发生,则B一定会发生)。

《土拨鼠之日》剧照。
你可能会说:“那好吧,或许我不能一举中第,但不断试错之后,我总会找到精确的谜底,不是吗?”事实上,想要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以试错的方式来有所收获的难度很大。以是那些试图通过频繁试错来取得进步的人,总被批作“老想着怎样才能把上一次的仗打得更好的将军”,更别提效果反馈通常还会滞后很长时间(有时甚至要等上几个月或几年才能看到)。此外,因果关系之间还存在概率性,有时候错误的行为反而带来了好效果,精确的行为反而引发不尽如人意的结局。雪上加霜的是,以试错的方式进修,往往连最基本的控制实验的尺度都无法满足,因为人们险些不可能做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对单独一个变量进行考证。我们也很少有机遇观察“反事实”,即若是采取了B步伐(或什么都不做)而非A步伐,效果会怎样。
然而,阻碍人们从经验中罗致教导的许多因素都是心理因素,而非环境因素。因此,本章将深入探讨一些主要的心理因素问题。首先需要声明的是,它们并不是区分“非专业人士”与科学家或其他专家的通用尺度。事实上,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每小我私家的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体现,科学家亦不破例,我们也将在接下来的两章中为这个观点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正如下一章所述,科学之以是可以或许(在某些情况下)屏蔽这些心理因素的不利影响,与科学家小我私家的品质或能力关系不大,科学方法和头脑习气才是重点,它们在帮助科学家克服人类自身局限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还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们将要探讨的这些心理因素并不是病态的,而是正常情况下人类认知能力的固有特质。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之以是普遍存在,极可能是因为具备了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因为在更系统的推理过程比较困难或费力的情况下,大多数类似的心理因素都能促使人类大脑运转得越发灵活高效。

《土拨鼠之日》剧照。
习气成自然
对本身控制的各项生活技能稍作观察后便会发现,你可以在险些无意识或少少意识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大多很多天常事务。想想你上一次需要刻意琢磨用多大气力踩油门、打开开关接热水或系鞋带是在何时?它们早已成为一种习气。习气可以让我们游刃有余地同时处理多项任务,还能节省精神,因为若是每做一件事都需要故意识地深入思考,只会令我们感觉“身心被掏空”(若是你实验过源自释教的正念冥想,想必就会相称有感触)。得益于人类大脑“自动”完成这些习气性事务的能力,我们才能将注意力投注在新事物上,好比一边开车一边听同车搭客讲述精彩的故事。习气在维持社会正常运作方面同样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将习气誉为“社会的巨大飞轮”。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以为:“文明的进步正是通过不断扩大人们在不经意间完成各种要务的数量来实现的。”
尽管习气并不是全无意识的行为,但因其发生疾速且轻松,我们往往难以对其深入观察和有效控制。在养成某项技能的初步阶段,我们仍有机遇观察到它对我们期望获得的效果产生的影响,进而决定对其进行重新调整还是直接舍弃不用。然而,随着技能运用变得越来越自然与自发,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也越来越难以仔细监控。所谓的“坏习气”指的就是功效失调的习气,因为是毫不费力的下意识行为,以是人们往往积习难改。总而言之,习气往往会指导人们做出无意识行为,从而成为阻碍人们从经验中罗致智慧的拦路石。

电视剧《暗黑》剧照。
启发和偏偏差
使人们难以从经验中进修的另外一系列因素,是人们在判断过程中存在的各种偏偏差,其往往导致人们忽视、歪曲或否认环境中至关重要的信息。与习气相似,偏偏差往往是因为人类大脑在注意力不足的情况下想要快速处理信息而产生的。当人们无法充分利用现有的证据时,偏偏差就是我们为草率决议支付的代价。
“有偏偏差”这个词可能已经在日常生活中被滥用了。我们往往能轻易地给别人扣上“有偏偏差”的帽子,只因我们无法认同他们的观点。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在第9章的探讨中就偏偏差的判断给出了相称客观的界说。回想一下,当某个探索过程产生大批随机误差时,我们通常会将这些误差称为“噪声”,而当该过程显示出系统性误差(即效果始终高于或低于精确谜底)时,我们则判断其存在偏偏差。因此,通过将某人的谜底与客观尺度或实在值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确定他是否存在偏偏差。然而,在客观实在无从得知的情况下,这个方法难以奏效,不过研究职员已经开发出多种可以消除偏偏差的实验性策略。
维基百科上有一份有据可查的认知偏偏差清单3,我们上次查阅时发现它已经收录了123个条目!乍看之下,你可能会想:仅靠“创造”各种偏偏差,心理学家就能过上光鲜富足的日子(不可否认,或许真有部分从业职员以此牟利)。这张清单中的很多认知偏偏差都是由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率先发现并纪录的。尽管特沃斯基于1996年不幸英年早逝,但卡尼曼后来凭借两人的共同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他的畅销书《思考,快与慢》(Thinking,Fast and Slow)中,卡尼曼给出了关于这些偏偏差的极为精彩的解读,在此猛烈推荐诸位买来读一读。

《思考,快与慢》,作者: [美国] 丹尼尔·卡尼曼 / [美国] Daniel Kahneman,版本: 中信出版社 2012年7月。
个中一些认知偏偏差的名称中就带有“偏偏差”一词(如证真偏偏差),另一些则被称为“启发”(如可得性启发)。尽管两个术语之间的边界很模糊,但“偏偏差”一词主要还是被用来描述效果(系统性地偏偏离了需要判断的实在值),“启发”一词则侧重于描述产生某种特定偏偏差的过程。“启发”是人类大脑为了快速做出判断而养成的一个特定习气,尽管绝对“简单粗暴且有效”(但容易堕落),却能逃避“绞尽脑汁地细细考虑”这项费力的认知事情。
我们可以借用“温度”的观点,各类偏偏差处在“冷”与“热”这两个极端效果之间的分歧位置。热偏偏差因其普遍性而易于描述,它们往往因情绪因素(尤其是愤怒或恐惊)和动机(我们期望发生什么或想要相信什么)而产生。位于另一端的冷偏偏差好像是人们在缺乏特定目标或欲望,处于平心静气的镇定状态时做出快速决断(人类典型的行为方式)的副产品。德国心理学家和行为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及其团队曾通过案例证实:人们通常会根据本身对城市名称的认识程度来推断城市规模的大小。4这种推断方法在多数情况下都是有效的,因为大城市通常要比小城市更出名,但它也会误导我们。比方,旧金山和圣何塞的人口离别约为81.5万和98.3万(后者人口多于前者),然而在大多数人看来,旧金山的城市规模肯定要大于圣何塞。这是为什么呢?不可否认,《你晓得去圣何塞的路吗》是一首朗朗上口的经典歌曲,但在流行文化中,旧金山的城市形象和元素显然出现得更多(毕竟这座城市以陡峭的山坡、奇特的缆车和金门大桥等标记性景物而闻名于世)。
本书将不会在热偏偏差上着墨过量,不是因为它们无足轻重,而是人们在发现此类偏偏差方面都很有经验。我们都曾见过被自身情绪和欲望蒙蔽了双眼的人,而且我们或多或少都曾在某个时刻陷入过类似的境地(即便我们不愿承认)。事实上,认知过程往往带有一定的动机性,即我们会由衷地期望某些信念和效果成为现实,另一些则不会成真。热偏偏差往往比冷偏偏差更具破坏性,因为人们为了得偿所愿,或许会无所不用其极地歪曲事实、抬高与本身意见相左的人。当有人坚持以为本身不偏偏不倚,但对方失之偏偏颇时,无法调和的矛盾就会产生。我们曾与在庭审过程中负责提供专家证词的诸多同行交换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以为,许多专家确实存在偏偏差,且接受一方的酬劳可能会形成利益冲突,但同时这些专家也大多坚称本身不会为五斗米折腰。
我们不打算将心理学文献中详细纪录的几十种偏偏差都悉数介绍一番,而是仅专注于阐明那些可能会阻碍人们从经验中罗致教导的认知偏偏差。

电视剧《暗黑》剧照。
过后诸葛偏偏差
有句老话叫作“过后诸葛亮”,其英文表述(Hindsightis20/20)借用了眼科术语“20/20”,意指在20英尺地方能看清事物的人,他的视力就是正常的,即拥有尺度距离的正常视力。若是你的视力检测效果为“20/40”,就说明你已经近视了。这句源自眼科术语的谚语所表达的意义就是,人们通常能在事件发生后轻易地给出精确的“预测”,毕竟放马后炮显然比有先见之明容易得多。心理学家巴鲁克·菲施霍夫(Baruch Fischhoff)曾表示,人类在下判断时有一个普遍特征,即人们在获知效果后往往会感觉它发生的幸免性好像比事前更不言而喻。
再举一例,在20世纪70年代初研究概率判断时,菲施霍夫选择了在他看来发生可能性极低或极高的一些事件,然后请人预测其发生的可能性。当时正逢尼克松总统执政期间,而且这位总统还曾是“反共先锋”。于是,菲施霍夫扣问了人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尼克松在卸任前对中国进行外交访问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低概率事件。)然而,尼克松确实在1972年访华了,此举令无数外交政策专家惊掉了下巴。菲施霍夫非常敏锐地对当初的受访者进行了二次回访,请他们试着回忆本身在尼克松访华可能性上给出的预测数值。他发现,人们于过后回忆出的“预测”概率普遍高于他们当初实际给出的概率。这些受访者清一色地(错误)表示,本身早就预判到了这个效果,即“早就笃定尼克松会访华”。
过后诸葛偏偏差给社科专业的先生酿成的影响尤为严重。在课堂上给先生们讲心理学或社会学的某项新发现时,我们发现他们会很智慧地自编理由,想象这些新发现产生的公道性,并言之凿凿地声称它们的存在早已有目共睹,甚至自我暗示本身早已猜到它们会被发现。为了在课堂上向先生们揭示这种偏偏差,我们通常会做如下实验:先给先生提供一段关于恋爱关系研究的简要描述,然后将先生分成两组并离别告知分歧的研究结论,个中一组先生得到的结论是“物以类聚”,另一组得到的结论是“异性相吸”。这两种说法固然都符合“常识”,却相互矛盾。遗憾的是,在阅读了所谓的研究效果后,两组先生中的大多数都倾向于以为本身看到的研究效果是“明确成立的”,甚至疑惑为什么老师要浪费时间去教这些显然人人都懂的内容。

电视剧《暗黑》剧照。
往常,过后诸葛偏偏差的显示方式可谓层出不穷,个中一些或许不会形成实质性的危险,另外一些却颇具破坏性。多年前,前橄榄球运动员兼演员辛普森因涉嫌谋杀前妻而被押上法庭。在讯断效果发表前,包括各领域专业人士(执业律师和职业赌徒)在内的大多数人普遍以为他被判有罪的可能性极大。在辛普森最终被宣判“无罪开释”后,我们本等候专家们能坦然承认本身的判断失误:
“哎呀,我们看走眼了。”实际情况却使人大跌眼镜,众多专家纷纷现身各大旧事节目“解释”道:黑人陪审员(占本案陪审团多数)都倾向于对黑人被告宽大处理。然而,当时的庭审数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若是专家们的确相信黑人陪审员存在维护同肤色被告的倾向,为何在庭审效果出来之前的预测中,他们没有预判到辛普森会被无罪开释呢?以是说,这些专家为了挽回颜面,过后编造了一个关于黑人陪审员存在偏偏见的理由。
证真偏偏差
我们把最精彩的部分留到了最后,而“最精彩”一词指的是我们最希望人们能克服的、影响最大的一种偏偏差。证真偏偏差指的是刻意寻找与自身假设相符的证据,并忽视与之相悖的证据。在控制了正反两面所有证据的情况下,若是我们更注重支持性证据而忽略了不和证据,也会产生证真偏偏差。同理,人们往往会对不利于自身假设的证据采取更严苛的审阅态度。证真偏偏差也存在冷、热两个极端,也包含分歧程度的偏偏误:热证真偏偏差较为常见,比方人们会选择性地只引用能让他们赢得争执或达成所愿的事实,或干脆否认不利于自身的事实证据。固然,冷证真偏偏差同样值得警惕:人们倾向于寻找和引用支持自身假设的事实,只是因为这好像是合乎逻辑的起点。毕竟,找不到任何证据支撑的假设基本不可能成立。但若是我们只寻找确证案例并止步于此,就会导致偏偏差。
原作者/索尔·珀尔马特 等
摘编/李永博
导语校对/卢茜
发布于:北京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