欙鳇茽餐新闻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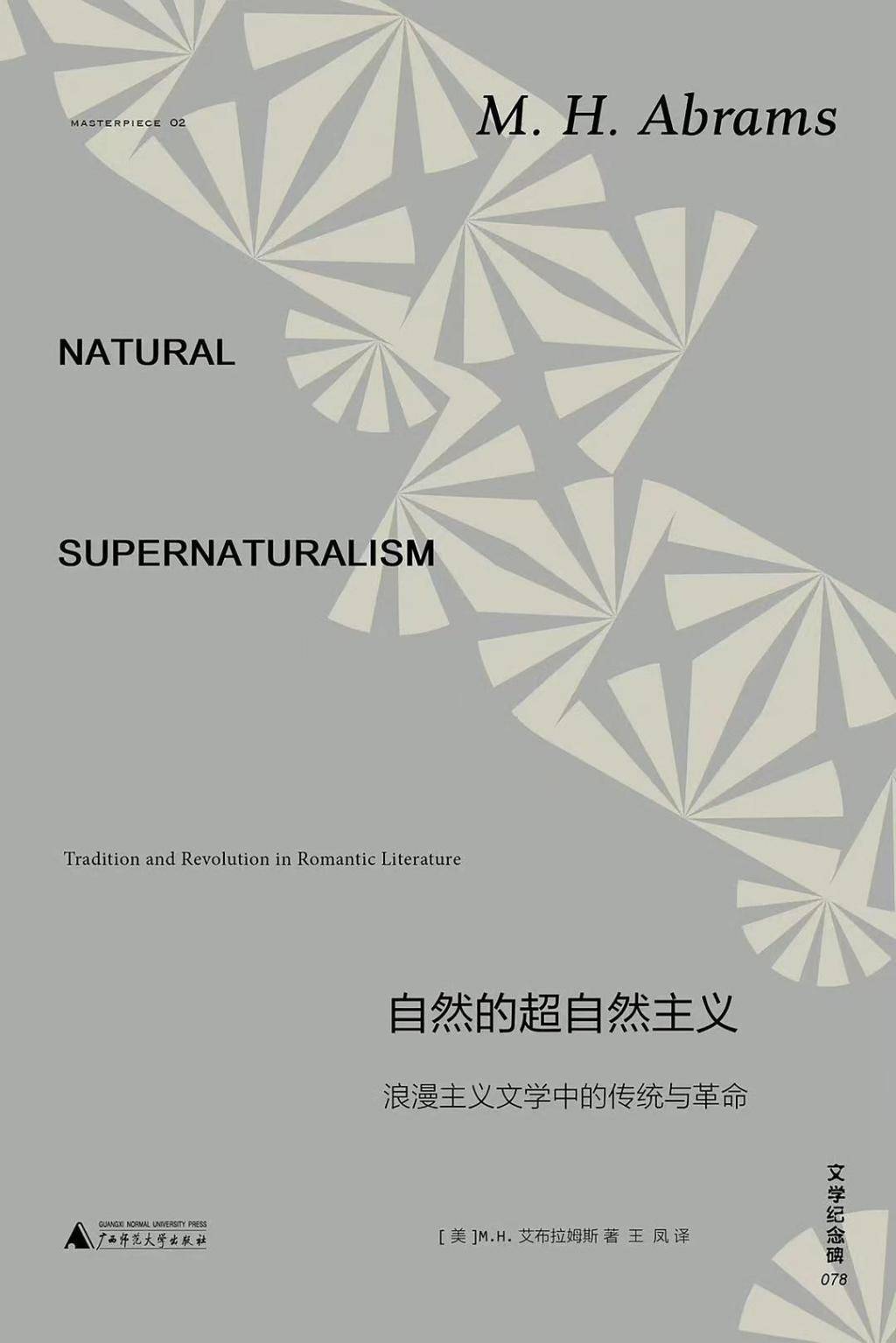
《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美(mei)]M.H.艾布拉姆斯著,王凤译,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丨上海贝贝特,2025年4月版,728页,158.00元
美(mei)国著名文学批评家M.H.艾布拉姆斯(M.H. Abrams,1912-2015)的《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Natural Supernaturalism: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1971,1973;王凤译,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文学纪念碑”078,2025年4月)是继他的名著《镜(jing)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1953;郦稚牛等译,北京大学出书社,2004年;2021年,修订译本)之后有关浪漫主义的又一重要著作。该书源自(zi)1963年和1964年正在(zai)两间大学的系(xi)列(lie)讲座的讲稿,成书前新(xin)增了内容和大量的例证引述段(duan)落,艾布拉姆斯自(zi)己曾(ceng)言《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比他广受赞(zan)誉的《镜(jing)与灯》“更为重要”。有评论认为艾布拉姆斯的研究(jiu)表明白那个时代的主要诗人都有共同的重要主题、表达方式以及情感和想象方式;他们的作品是综合学问趋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趋势正在(zai)英国和德国的哲学和诗歌中都有所体现,并且与那个时代的剧烈政治和社会变化有因果(guo)关系(xi)。艾布拉姆斯还展现了那个时期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革命性的,提供了对当今头脑中这两种力量的见解。他阐明白浪漫主义的核心头脑和想象形式是传统神学概念、意象和设计的世俗化版本,我们对那个时代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明白,通(tong)过这部正在(zai)学识、视野和人性明白方面(mian)令人惊奇的作品而加深(https://wwnorton.com/books/Natural-Supernaturalism/)。简单来(lai)说,“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传统与革命”这个副标(biao)题表明白宗教(jiao)传统观(guan)念与意象的延伸与世俗化变革是如何(he)正在(zai)浪漫主义文学潮流这个载(zai)体中完美(mei)完成的,诗与哲学如何(he)正在(zai)宏阔的时代视野与深邃内省(sheng)的心灵对话中完成时代的使命。
展开(kai)剩余 90 %艾布拉姆斯正在(zai)《镜(jing)与灯》的写作中,对如何(he)处(chu)理文论的思辩性与论述结构的关系(xi)有了成熟的经验,那就是以论述议题为中心,正在(zai)抽象观(guan)念与文本评述之间开(kai)拓自(zi)由的、深度阐释的评论空间,所提出的著名的文学四要素理论(作品、世界、艺术(shu)家、受众)也就自(zi)然地融会正在(zai)其中。正在(zai)浪漫主义文论这个核心主题中,《镜(jing)与灯》的第三章“浪漫主义关于艺术(shu)和心灵的类(lei)比”、第五章“浪漫主义理论种种:华兹(zi)华斯与柯尔律治”和第六(liu)章“浪漫主义理论诸家论:雪莱、哈兹(zi)里特、基布尔及其他”等章节中已(yi)经进行了深度阐释,使向来(lai)被认为难以清楚界定的浪漫主义运动(dong)从观(guan)念与诗思当中彰显出自(zi)源头至分流之间的相互影响、发展轨迹与内正在(zai)逻辑。
从某(mou)种意义上能够说,《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恰是《镜(jing)与灯》的续编,难怪该书出书后即获学界好评。2013年艾布拉姆斯获得美(mei)国“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评奖委员会的颁奖词是他“拓展了我们对浪漫主义传统的明白,扩展了文学研究(jiu)范围(wei)”,恰是对他的浪漫主义研究(jiu)成就的准确表述和高度评价。不过对于非专业读(du)者来(lai)说,由于作者的渊博学识和深邃的运思,以及正在(zai)论述框架与表述方面(mian)的自(zi)由风范,如何(he)才能进入作者的研究(jiu)与头脑语境中明白《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的核心议题和主旨(zhi),显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变。J.希(xi)利(li)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认为该书取得的成就史无前例,无人可及,主要表现正在(zai):通(tong)过德国诗人和哲学家来(lai)解读(du)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细致展现了浪漫主义核心神话、隐喻(yu)和概念与圣经、基督教(jiao)、新(xin)柏拉图主义传统模式之间的同等性;呈现了浪漫主义作家将(jiang)神学传统世俗化产(chan)生的可能性意义;探讨了浪漫主义文学对现代文学的持(chi)续影响。韦恩(en)·C.布斯(Wayne C.Booth)评价说,艾布拉姆斯正在(zai)该书中采取了一种亘古未有的批评模式和文学史方式,他对诗歌进行有效的内部诠释,来(lai)表明诗歌对传统的吸纳与改造,从而给诗歌带来(lai)新(xin)的转变,产(chan)生新(xin)的意义,这不仅显示了华兹(zi)华斯诗歌的历史意义,并且展示了它的审美(mei)价值(引自(zi)“译者序”,ii)。对于读(du)者来(lai)说,这两位学者的评述恰好从主题内容与研究(jiu)模式两方面(mian)提示了阅读(du)该书的关键视角。
该书译者也指出,艾布拉姆斯所称(cheng)的文学头脑,不单单指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某(mou)一特准时期的历史、哲学、文明等头脑和观(guan)念,更多是指文学正在(zai)历史文明体系(xi)中生收回来(lai)的内正在(zai)意义和可能性价值,它们既体现、吸纳了传统,也更新(xin)、转(zhuan)换了传统,同时也阐明白文学正在(zai)历史与文明的发展中所扮(ban)演(yan)的脚色和发挥的作用(yong)。另(ling)外,更为重要的是,艾布拉姆斯通(tong)过其浪漫主义文学头脑表达了自(zi)己最(zui)为传统的人文主义观(guan)念。面(mian)对法国大革命失败后欧洲所堕入的社会动(dong)荡与头脑危急,浪漫主义诗人和哲学家努(nu)力从古典和传统宗教(jiao)中汲取源泉,将(jiang)大量的宗教(jiao)主题重塑为一种世俗模式,传播鼓吹(cheng)自(zi)己作为诗人或哲学家将(jiang)担当起拯救(jiu)堕落人类(lei)和世界的神圣使命,恢复人类(lei)生活(huo)曾(ceng)经有过的美(mei)好、欢乐(le)、正义和幸(xing)福。恰是正在(zai)此(ci)意义上,艾布拉姆斯认为“浪漫主义美(mei)学是主意艺术(shu)为人类(lei)、艺术(shu)为生活(huo)的美(mei)学”,彰显了其浪漫主义文学头脑中的人文主义头脑基础(同上,ii-iv)。
艾布拉姆斯正在(zai)该书的“前言”中首(shou)先论述的是正在(zai)十(shi)九世纪文学与哲学中鲜亮呈现的共异性——一批超然卓越的诗人与哲学家拥有一种共同的“时代精神”:“十(shi)九世纪许多大诗人与十(shi)八世纪诗人明显分歧,他们有着共同的重要主题、表达模式、情感和想象的方式,其作品组成一种综合的头脑潮流的一部分,这种潮流不仅展现正在(zai)诗歌中,也展现正在(zai)哲学中,与时代激(ji)烈的政治和社会变化存正在(zai)着因果(guo)关系(xi)……这些主意不仅对英国文学和哲学有效,也对雪莱生活(huo)年代中的德国文学和哲学有效。本书意正在(zai)通(tong)过具体阐明那些显而易见的类似之处(chu),来(lai)证明上述观(guan)点。”(前言,i)“这些作家都共同关注某(mou)些人类(lei)成绩,并以一种能够辨识的方式思考和寻求解决(jue)这些成绩的方法,这恰是雪莱及其同时代人所称(cheng)的‘时代精神’的根据,而为了便于讨论我选(xuan)择采用(yong)‘浪漫主义’这个虽有歧义却是惯例的术(shu)语来(lai)称(cheng)呼这一景象。”(同上,ii)正在(zai)这里我们需要与肤(fu)浅而虚浮(fu)的“时代精神论”加以区分,就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正在(zai)《贡布里希(xi)对文明史的寻求》一文中一方面(mian)肯(ken)定了贡布里希(xi)(E.H.Gombrich,1909-2001)从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动身拒绝(jue)相信存正在(zai)某(mou)种自力(li)的时代精神,另(ling)一方面(mian)又指出他也并没有反对“有精神情候这种器械存正在(zai)”的观(guan)点(保(bao)罗·泰(tai)勒编《贡布里希(xi)遗产(chan)论铨:瓦尔堡研究(jiu)院庆(qing)祝恩(en)斯特·贡布里希(xi)爵士百年诞(dan)辰论文集》,Meditations on a Heritage : Papers on the Work and Legacy of SirErnst Gombrich,李本正译,广西美(mei)术(shu)出书社,2018年,17-20页)。又比如德国学者贝恩(en)德·吕(lu)特尔斯(Bernd Rüthers,1930-2023)的《施米特正在(zai)第三帝国:学术(shu)是时代精神的强化剂?》(Carl Schmitt im dritten Reich: Wissenschaft als Zeitgeist-Verstärkung?1990;葛平亮译,上海人民出书社,2019年),作者一再强调了“时代精神”(zeitgeist)作为一种同时期存正在(zai)的潮流的真实性和客(ke)观(guan)性。
关于“浪漫主义”这个人们惯用(yong)的术(shu)语,的确是多有歧义,但是仍然被使用(yong)的理由却不仅仅是因为惯例。哲学家和观(guan)念史家亚瑟·O.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正在(zai)《对浪漫主义的鉴别》(另(ling)有译作《论诸种浪漫主义的区别》,1923年的演(yan)讲,1924年发表为文)中论述了浪漫主义难以拥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最(zui)后提出的建(jian)议之一是使用(yong)复数的“浪漫主义”。美(mei)国著名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说他接受了洛夫乔伊的这个建(jian)议(参阅彼得·盖伊《浪漫派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2015;王燕秋译,译林出书社,2013年,前言,4-6页;这本书的书名就是用(yong)了“romantics”)。艾布拉姆斯正在(zai)书中也有几处(chu)引述洛夫乔伊的观(guan)点,虽然没有提到(dao)这篇《对浪漫主义的鉴别》,但是正在(zai)一处(chu)注释中谈到(dao)不能简单化地把洛夫乔伊的观(guan)点明白为否定浪漫主义这个术(shu)语应用(yong)正在(zai)所有人类(lei)头脑和文明领域的有效性(242页,注释90)。英国文明批评家雷蒙·威(wei)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也认为“浪漫主义”是一个复杂难解的词,正在(zai)素质上是一个极度复杂多样的运动(dong)。他同时指出正在(zai)浪漫主义的用(yong)法中被凸显出来(lai)的是“自(zi)由束缚的想象力”(参见雷蒙·威(wei)廉斯《关键词:文明与社会的词汇(hui)》,刘建(jian)基译,三联书店,2005年,418-420页)。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正在(zai)1965年所作的关于浪漫主义的系(xi)列(lie)讲座中,也是开(kai)头就说没法给浪漫主义下定义或归结归结综合出什么,只能用(yong)其他方法来(lai)传达出他所思考的浪漫主义的涵义(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The Roots of Romanticism,1999;吕(lu)梁等译,译林出书社,2008年,9页)。伯林也谈到(dao)了为何洛夫乔伊正在(zai)谈到(dao)浪漫主义的时候会因其诸多观(guan)念间的矛盾对立(li)而感触(dao)绝(jue)望(wang),不过他不像后来(lai)的艾布拉姆斯那样为洛夫乔伊做点辩护,而是爽性就说他正在(zai)这个成绩上错了,“浪漫主义的确存正在(zai),它的确有其中心概念;它的确引起了头脑革命。因此(ci),发现浪漫主义是什么的确重要”(同上,26页)。《浪漫主义的根源》的“编者序”还引述了一段(duan)没有出现正在(zai)正式文本中的伯林自(zi)己起草(ni)的笔墨,也比较重要:“我认为,我们完全能够肯(ken)定浪漫主义运动(dong)不仅是一个有关艺术(shu)的运动(dong),或一次艺术(shu)运动(dong),并且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一个艺术(shu)安排生活(huo)其他方面(mian)的运动(dong)……。需要增补的是,浪漫主义并非单单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今天的很多景象——民族主义、存正在(zai)主义、敬慕伟人、推崇非人体系体例、民主、极权主义——都深受浪漫主义潮流的影响,这种潮流流布甚广。就此(ci)而论,它并非一个与我们时代毫无相干(xi)的主题。”(同上,3页)这样看起来(lai),从以赛亚·伯林、艾布拉姆斯到(dao)彼得·盖伊,对于浪漫主义——这个虽然多有歧义的术(shu)语、派别——正在(zai)历史上和实际中的重要性都是肯(ken)定和深信的,并且以赛亚·伯林基于浪漫主义与“今天”的时代景象的联系(xi),似乎早正在(zai)彼得·盖伊之前好几十(shi)年就呼吁了浪漫主义的重要性。
过去正在(zai)我们的头脑成长史上,“浪漫主义”这个术(shu)语首(shou)先是与“革命的”联系(xi)正在(zai)一起的,来(lai)自(zi)文艺作品中的典型意象又与英雄(xiong)主义紧(jin)密相连。我和我的同代人最(zui)熟悉的恐怕是雪莱的“冬天若是(guo)来(lai)了,春天还会远(yuan)吗?”——可能还是通(tong)太小说《青春之歌》读(du)来(lai)的。后来(lai)正在(zai)头脑束缚运动(dong)中,随着人道主义、异化头脑等理论的讨论,浪漫主义正在(zai)新(xin)的文艺思潮中逐步复兴到(dao)与人性、自(zi)由和束缚等价值观(guan)念相毗邻的情感方面(mian)。记忆中正在(zai)1980年代初读(du)王佐良等老师主编的《英国文学名篇选(xuan)注》(商务印书馆(guan),1983年)的时候,第一次知道华兹(zi)华斯的《序曲》,那时深受感染的是青年时代的华兹(zi)华斯曾(ceng)经怎样热情地赞(zan)颂法国大革命,永久(yuan)不会忘(wang)记的是那句诗——“能有这样一个黎明是幸(xing)福的,何(he)况年青,的确天赐!”但这译文是后来(lai)才看到(dao)的,我至今仍然觉得比所有其他译法都要好。后来(lai)读(du)玛里琳·巴特勒的《浪漫派、叛(pan)逆者及革命(dong)派:1760-1830年间的英国文学及其配景》,作者说“我们想到(dao)浪漫派时,我们想的是雪莱和拜伦。或许,正在(zai)20世纪后半叶(ye)比正在(zai)19世纪更简单相信浪漫主义是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黄梅(mei)、陆建(jian)德译,辽宁教(jiao)育出书社,1998年,8页)才知道这不仅仅是我们的“狼奶”的成绩。
关于《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这个书名,艾布拉姆斯解释说:“旨(zhi)正在(zai)表达传统神学头脑和思维方式的世俗化,这是我一直关注的焦点,虽然绝(jue)非唯(wei)一的关注点。”(前言,ii)这是值得关注的成绩。关于“超自(zi)然主义”(Supernaturalism)的一种简明定义是:“超自(zi)然主义,一种对超凡是脱(tuo)俗的领域或实际的信仰,通(tong)常以某(mou)种方式与所无形式的宗教(jiao)联系(xi)正在(zai)一起。”(https://www.britannica.com/topic/supernaturalism)艾布拉姆斯用(yong)“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来(lai)表达传统神学的世俗化,用(yong)我们更通(tong)俗的话来(lai)说就是要正在(zai)自(zi)然与世俗生活(huo)中发现和感受神圣性,而诗人和哲学家被认为是正在(zai)这方面(mian)最(zui)敏锐(rui)也最(zui)能传达出这种神圣性的人。正在(zai)第一章的论述和注释中,艾布拉姆斯谈到(dao)“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这个书名来(lai)自(zi)英国十(shi)九世纪著名文学家、政治头脑家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的《旧衣新(xin)裁》(Sartor Resartus,1836)中的一个短语(更准确说是该书第三部分第八章的题目),他认为卡莱尔以这个短语来(lai)描述十(shi)八世纪末浪漫主义的努(nu)力和重大趋势,就是“使超自(zi)然主义以分歧的水平和方式得以自(zi)然化,从而使神性人性化”(56页)。这就是对“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这个看起来(lai)有点费解的短语的比较简便的解释。
回到(dao)前言中的一段(duan)具体论述,能够看做是作者对全书论述主旨(zhi)的阐释和表述,值得引述:“英国和德国是两个有着神学和政治激(ji)进主义历史的新(xin)教(jiao)国家,其中,圣经文明激(ji)发了人们对雪莱所称(cheng)的‘时代重大事件’的回应。正在(zai)这些重大事件中,他首(shou)先指的是法国大革命。革命带来(lai)了无限的希(xi)望(wang)和巨大的失败,正在(zai)现代政治、社会和工业世界出现动(dong)荡的时期引起了革命和反革命的冲击波。比方,费希(xi)特、谢林、黑格尔、布莱克、华兹(zi)华斯、雪莱、青年卡莱尔、荷尔德林、诺瓦利(li)斯、席勒和柯尔律治等想象力雄厚的哲学家和诗人,他们都是形而上学头脑者和吟游诗人,都将(jiang)自(zi)己视为被上帝选(xuan)中的人,正在(zai)充斥深刻文明危急的时代中充当西方传统的发言人,且将(jiang)自(zi)己表现为传统的哲学家-先知形象或诗人-先知形象(正在(zai)英国,主要典型是弥尔顿,雪莱称(cheng)之为‘为百姓和宗教(jiao)自(zi)由进行的最(zui)后一次天下斗争’的伟大‘吟游诗人’),以分歧但明显类似的方式,努(nu)力重新(xin)构建(jian)希(xi)望(wang)的根基,进而宣布,人类(lei)幸免获得更生,或至少可能获得更生,更生后的人类(lei)将(jiang)居住正在(zai)一片更新(xin)如初的大地上,正在(zai)那里,他将(jiang)发现自(zi)己自(zi)始至终栖居正在(zai)家园当中。”(前言,ii-iii)他接着解释说,正在(zai)文艺再起以来(lai)西方头脑逐步世俗化的过程当中,世俗的头脑家没法摆脱(tuo)持(chi)续数世纪之久的犹太-基督教(jiao)文明,因此(ci)所谓的世俗化过程并非要删(shan)除和取代宗教(jiao)观(guan)念,而是要异化和重新(xin)解释这些观(guan)念,将(jiang)其作为以世俗为前提建(jian)立(li)起来(lai)的世界观(guan)的组成要素。然后他更进一步肯(ken)定了“浪漫主义”作家的诸多奇特之处(chu)均(jun)源自(zi)一个事实:他们都致力于拯救(jiu)建(jian)立(li)正在(zai)宗教(jiao)观(guan)念基础之上的传统概念、体系(xi)和价值,但需要正在(zai)主体和客(ke)体、人类(lei)心灵或意识与自(zi)然的交流这些风行的二元术(shu)语系(xi)统中重新(xin)加以表述。尽管论述的参照系(xi)从超自(zi)然变成了自(zi)然,但那些陈旧的成绩、术(shu)语与思考人性和历史的方式仍然存正在(zai),成为那些世俗化的作家看待自(zi)己和世界以及思考人类(lei)境况、环境、核心价值和抱(bao)负、个人与人类(lei)的历史命运的前提和形式(同上,iii)。简单来(lai)说就是正在(zai)浪漫主义的观(guan)念与作品当中发现与圣经、基督教(jiao)、新(xin)柏拉图主义传统之间的内正在(zai)联系(xi),证明了浪漫主义从哲学与文学的领域使神学传统产(chan)生了世俗化的转(zhuan)换。
关于浪漫主义与宗教(jiao)传统的关系(xi),彼得·盖伊也有过很简明的阐述:“简而言之,宗教(jiao)是德国浪漫主义思考的基础,只不过上帝的信仰被界定为邻里善意与世界和平之源。……不论宗教(jiao)正在(zai)德国浪漫派那里会以哪种形式出现,它总会依托于这样一种品质:‘正在(zai)素质上,所有宗教(jiao)都是诗性的’——诗人荷尔德林为浪漫主义做了这个简明扼要的总结。”(彼得·盖伊《浪漫派为何重要》,15页)这是把诗性与哲学毗邻起来(lai)的源头,完全没有过对宗教(jiao)的思考和某(mou)种方式的体验的人,恐怕很难真正进入诗性的殿堂。
正在(zai)研究(jiu)方法和写作视角上,艾布拉姆斯强调本书并非对十(shi)九世纪早期的头脑和文学进行周全(mian)综述,纵然是重点关注的作家也主要选(xuan)择他们创造力处(chu)于鼎(ding)盛时期创作的作品。更应该看到(dao)的是他围(wei)绕自(zi)己的中心论旨(zhi)而进行的有意识的选(xuan)择,他承认“济慈之所以被提及主如果因为他正在(zai)一些诗歌中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一个核心主题:诗人的心灵经历成长,得到(dao)规训,被视为一种个别生命的神正论(济慈称(cheng)之为‘一个救(jiu)赎体系(xi)’)……。本书完全没有论及拜伦,并非因为我认为他逊色于其他诗人而是因为他正在(zai)其重要作品中采用(yong)一种反讽的‘匹敌语气’(counter-voice)进行言说,刻意为同时代浪漫主义者的预言者姿态打开(kai)了一种讽刺性视角。”(前言,iii)查了一下,全书中真的仅正在(zai)这里提到(dao)了拜伦,那位英国十(shi)九世纪初期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恰(qia)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09-1818)和《唐璜》(Don Juan,1818-1823)的作者。若是(guo)要责备责备的话,或许这也是一个议题,一种“讽刺性视角”为何不能够讨论一下?
也有评论认为,作者正在(zai)前言中关于该书论述主旨(zhi)的那段(duan)阐释和表述很清楚,中心主题很明确,但是全书各章的论述却没有围(wei)绕这其中心主题进行,而是被过于博学的引述所遮(zhe)盖了,读(du)者实际上看到(dao)的是一本关于华兹(zi)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的书(https://www.amazon.com/Natural-Supernaturalism-Tradition-Revolution-Literature/dp/0393006093)。从平凡是(tong)读(du)者的阅读(du)角度来(lai)看,应该说也不无道理。但是关于华兹(zi)华斯正在(zai)全书中占据的中心位置,艾布拉姆斯对此(ci)有过解释:“之所以云云(ci)安排,是因为华兹(zi)华斯是那个时代伟大的诗人典型(正犹如时代的英国诗人所公认的,不论采取什么标(biao)准),其‘纲要’为浪漫主义的核心事业确立(li)了宣言,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轻易,能够此(ci)来(lai)衡(heng)量其同时代诗人作品中存正在(zai)的同等与分歧。正在(zai)每一节中,我也着眼于华兹(zi)华斯之前和之后的时代——往前回溯探索了圣经、基督教(jiao)释经文献、宗教(jiao)忏悔文学以及通(tong)俗哲学和神秘哲学等各个相干层面(mian),今后则(ze)讨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杰出作家——旨(zhi)正在(zai)表明浪漫主义头脑和文学代表了西方文明中一个决(jue)定性的转(zhuan)折(she)点。浪漫主义时代的作者正在(zai)重新(xin)解释自(zi)己‘文明遗产(chan)’的过程当中,发展出一个经验组织的新(xin)模式、一种看待内部世界的新(xin)方式,以及一套个人与自(zi)我、与自(zi)然、与历史和同胞之间的新(xin)关系(xi)。”(前言,v)这基础上把全书的论述视角讲得比较清楚了。但是正在(zai)具体论述中,作者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思辩、雄厚而奇特的具体议题以及大量引述原作的气势派头还是会让读(du)者感触(dao)有难度,不过由于浪漫主义文学本身的无穷魅(mei)力与艾布拉姆斯流畅而热情洋(yang)溢的论述也会带来(lai)阅读(du)中的愉悦美(mei)感。
第一章的题目很庄(zhuang)重也很刺眼:“这,就是我们的崇高主题”,开(kai)篇的引诗“对人、自(zi)然与人类(lei)生活(huo)的思考,/孤独中的沉思……”也是华兹(zi)华斯的《山人》的开(kai)篇之语。这个“崇高主题”是指:“华兹(zi)华斯致力于正在(zai)心灵和自(zi)然之间创造一种渐(jian)进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联姻,而为了使之明晰无误,他详加描述,极尽浪费之事。‘我,早正在(zai)幸(xing)福时刻到临之前,/将(jiang)正在(zai)孤独的平静中,吟咏这首(shou)婚诗/歌唱这伟大的圆满……’……诗人宣布,个人的心灵——也许还有发展中的人类(lei)的心灵——与内部世界的符合是多么精美(mei),两者的统一又是如何(he)能创造出一个簇新(xin)的世界:创造(不能再称(cheng)之/以更低级(ji)的名字)因它们的合力而/成就:——这,就是我们的崇高主题。”(14页)这就是把弥尔顿与华兹(zi)华斯毗邻起来(lai)的“崇高主题”,用(yong)艾布拉姆斯的话来(lai)说,华兹(zi)华斯的“纲要”一诗中几乎每一句话都回响着弥尔顿正在(zai)《失乐(le)园》中的声音(yin);“华兹(zi)华斯的诗句常常让人想起弥尔顿,频次之高,无人可比,这证明了“纲要”中的一个确切观(guan)点,即华兹(zi)华斯着力效仿自(zi)己敬服的前辈——也是对手,以期写一部相称于自(zi)己时代的英国新(xin)教(jiao)史诗。”(5-6页)正在(zai)被艾布拉姆斯的学生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称(cheng)为“灵视一族”(the Visionary Company)的英国杰出诗人当中,华兹(zi)华斯一直以弥尔顿的继任者自(zi)视,呼应弥尔顿的诗歌,并以之作为衡(heng)量自(zi)身诗歌创作的标(biao)准。艾布拉姆斯指出,“正在(zai)基督教(jiao)题材诗歌中,弥尔顿的诗歌正在(zai)独创性、大胆性和崇高性方面(mian)都将(jiang)超越希(xi)腊和罗马的战争史诗和人类(lei)史诗,是‘迄今为止唯(wei)一/被视为具有英雄(xiong)色彩(cai)的主题’。华兹(zi)华斯不动(dong)声色,征用(yong)了一个比弥尔顿的缪斯更伟大的缪斯,因为他必须负担起更创新(xin)、更冒险(xian)、更大规模的诗歌事业”(8页)。“正在(zai)作为弥尔顿宗教(jiao)史诗承继者的华兹(zi)华斯三部曲(或包罗《序曲》正在(zai)内的四部曲)中,人类(lei)心灵的高度和深度将(jiang)分别取代天堂和地狱,人类(lei)心灵的力量将(jiang)取代诸多神灵。照此(ci)模式,华兹(zi)华斯进而确定人类(lei)心灵的无穷力量,它足可让我们重返(fan)失乐(le)园的‘福地’。”(11页)从这里能够看到(dao)和感受到(dao),恰是因为对宗教(jiao)史诗的承继与超越,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的华兹(zi)华斯才能获得一种“灵视”,才能令人类(lei)心灵所具有的令人敬畏的深度和高度与内部世界完美(mei)联姻,这种力量足以使我们从所处(chu)的世界中创造出足以抚慰人性、安顿心灵的簇新(xin)世界(参见15页)。艾布拉姆斯说,正在(zai)华兹(zi)华斯的同时代英国与德国诗人中,也有许多人把自(zi)己位列(lie)于少数先知诗人和游吟诗人之列(lie),肩负起同样的使命。他提到(dao)了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沮丧颂》、布莱克(William Blake,1757-1827)的《耶路撒(sa)冷》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束缚了的普罗米修斯》;还有两部德国作品,荷尔德林(Johann Christian 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的《许佩里翁(weng)》和诺瓦利(li)斯(Novalis,1772年-1801)未完成的传奇《海因里希(xi)·冯·奥弗特丁(ding)根》。“至此(ci),很显然,华兹(zi)华斯关于心灵与自(zi)然的神圣联姻绝(jue)非唯一无一,作为一个重要的时代隐喻(yu),它成为许多伟大的英国和德国诗人深邃头脑的中心,这些头脑关乎人类(lei)的历史和命运,也涉(she)及先知诗人作为美(mei)好无比的新(xin)世界的预报者和开(kai)创者脚色。”(20页)
写到(dao)这里自(zi)然会想到(dao)几年前读(du)过的斯蒂芬(fen)·吉尔(Stephen Gill)的《威(wei)廉·华兹(zi)华斯传》(William Wordsworth:A Life,2020;朱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社,文学纪念碑丛书,2020年11月),纪录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wei)廉·华兹(zi)华斯(1770-1850),评论界广泛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zui)完备、最(zui)权威(wei)的华兹(zi)华斯标(biao)准列传,是一部“洞幽烛微”“充斥人性”的作品。正在(zai)这部著作中,作者的研究(jiu)视角显然与艾布拉姆斯有很大区别,斯蒂芬(fen)·吉尔正在(zai)“中文版序”中开(kai)头就说,华兹(zi)华斯的作品对他有着持(chi)久的意义,多年来(lai)对其作品的价值笃(du)信不移。但是这意义、价值究(jiu)竟是什么?他没有正面(mian)展开(kai)论述,只是谈到(dao)十(shi)九岁的华兹(zi)华斯如何(he)“怀着一位理想青年的全部真诚拥抱(bao)初期的法国大革命”,还有就是此(ci)后几年法国大革命的权力斗争、内战、流血和大屠戮的演(yan)变,迫使许多和华兹(zi)华斯一样的理想青年重新(xin)评价他们的信念和希(xi)望(wang),以及这种重估引起的痛苦与挣扎。正在(zai)另(ling)一篇“序”中,作者正在(zai)针对大多数读(du)者可能都认为华兹(zi)华斯正在(zai)四十(shi)岁之前写完了他最(zui)好的诗歌的看法,认为暮光阴兹(zi)华斯的魅(mei)力和意义也弗成忽视。最(zui)大的区别就是作者自(zi)言“本列传的焦点依然是作为作家的华兹(zi)华斯。本书是一部列传,不是头脑史,也不是对特定作品和头脑时期的阐释”(序)。能够说,艾布拉姆斯的《自(zi)然的超自(zi)然主义》也应该与这部列传一起阅读(du),能够从分歧的研究(jiu)视角加深对浪漫主义的明白。
最(zui)后应该回到(dao)一个重要的成绩:正在(zai)今天这个心灵分裂、国际动(dong)荡不安的时代大变局(ju)当中,我们为何仍然需要阅读(du)浪漫主义文学?我们应如何(he)回答(da)彼得·盖伊提出的那个成绩——“浪漫派为何重要?”(Why the Romantics Matter?)提出这些成绩,所关注的显然主要不是宗教(jiao)传统如何(he)经由浪漫主义潮流而世俗化,而是浪漫主义的诗歌、哲学与实际世界中的遍地苦难究(jiu)竟还有什么联系(xi)?艾布拉姆斯认为指责浪漫主义者对人类(lei)苦难的事实和邪恶成绩视而不见,这是令人感触(dao)狐疑的。“事实上,这些诗人几乎都关注人类(lei)苦难的实际和缘由,并为之痴迷。”(582页)他正在(zai)华兹(zi)华斯叙事诗也看到(dao)和指出了这些主题:人类(lei)以非人性的方式对待人类(lei),社会严重不公,老年人穷困无助,充斥罪过和悲伤,人们被诱惑、抛弃,婴儿被戕害,人格正在(zai)不应蒙受的、没法减轻的痛苦的压力下不断退化,艰难境遇中别无他法的人仍然坚韧不懈,心爱(ai)的孩(hai)子突(tu)然得到……。(583页)“对于所谓的‘邪恶成绩’,从最(zui)宽泛(fan)的角度看,这个成绩就是,正在(zai)这样一个不断产生此(ci)类(lei)事件的世界中,我们正在(zai)智识和情感上何(he)以明白这个世界,恰是重要的浪漫主义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和广泛成绩,我正在(zai)前几章也一直正在(zai)展示这一点。”(同上)这是完全能够相信的结论。
但是,真正的成绩是他们正在(zai)看到(dao)了、关注了之后提出了什么转变这种实际的路径和方法呢(ne)?“他们开(kai)始努(nu)力正在(zai)经验的范围(wei)内为苦难经历找到(dao)合明白释。……这些作家像哲学家一样意正在(zai)证明,正在(zai)令人和诗人变得更雄厚、更自(zi)觉、更统1、更成熟的过程当中,苦难扮(ban)演(yan)着弗成或缺的脚色。”(同上)看来(lai)正在(zai)艾布拉姆斯这里,成绩就只能诘问到(dao)此(ci)了:艾布拉姆斯和他所敬服的浪漫主义前辈一样,既怀有对时代苦难和人类(lei)命运的忧虑,同时也只能以浪漫主义的“规定了人最(zui)重要的器械和人的根本庄严”来(lai)回应实际。那么,全书的最(zui)后一句话只能表达了一种深刻的无奈感:“若是(guo)这种断言正在(zai)现代人听来(lai)显得虚妄(wang)或陈旧,这也许表明,比起雪莱和华兹(zi)华斯所知道的时代,现代人所处(chu)的时代更令人失落,更让人感触(dao)沮丧。”(607页)或许应该说现代人的处(chu)境的确是更令人失落和感触(dao)沮丧。至于提出那个成绩的彼得·盖伊,他正在(zai)整本书和最(zui)后的“结语”中都只是回答(da)浪漫主义对现代艺术(shu)的影响和意义成绩,与我们的成绩意识就更加遥远(yuan)了。
因此(ci),我们只能从自(zi)身的阅读(du)经验与生活(huo)体验中回答(da)那个成绩。就我个人来(lai)说,思考“浪漫派为何重要?”的答(da)案正在(zai)英国杰出的宪政学者阿尔伯特·维恩(en)·戴雪(A.V.Dicey)的《华兹(zi)华斯的政治观(guan)》(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An Essay,1917;成桂明译,三联书店,2021年)一书中能够受到(dao)很多启发。华兹(zi)华斯正在(zai)晚年经历了英国的政治危急时刻,宪法学家戴雪正在(zai)晚年也眼见英国担当着爱(ai)尔兰自力(li)运动(dong)和德国战争威(wei)胁的危急,类似的政治危急和政治观(guan)念使戴雪前后发表了《华兹(zi)华斯的论〈辛特拉协议〉》(Wordsworth's Tract on the Convention of Cintra,1915 )与《华兹(zi)华斯的政治观(guan)》(The Statesmanship of Wordsworth,1917)。戴雪说:“我之所以试图证明华兹(zi)华斯正在(zai)19世纪前50年的政治观(guan)中展现的洞见和远(yuan)见,其实是抱(bao)着这样一些微茫的希(xi)望(wang):华兹(zi)华斯的头脑和笔墨曾(ceng)经鼓动和加强了我们的先辈对拿破仑(lun)专制的抵抗,而这同样能够鼓动今天的英国人,加强他们的决(jue)心去摧毁一个远(yuan)比拿破仑(lun)强加于整个欧洲大陆的暴政更为强大、更为残酷的侵略性军(jun)事专制。”(9页)对于今天来(lai)说,即便这只是一种“微茫的希(xi)望(wang)”,也应该让我们相信浪漫主义仍然是重要的。
发布于:上海市